张剑:有温度的历史藏在日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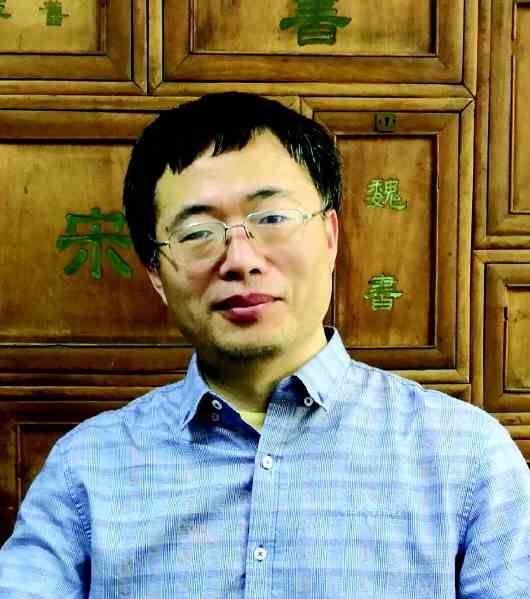 □特约撰稿尧育飞
□特约撰稿尧育飞
“日记”文献最早可溯源于西汉时期,此后经宋元两代的发展,至明清时期蔚然大观。晚近以来,大量“日记”的刊行,丰富了研究材料,对文史研究有颇多推进。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文学遗产》副主编,张剑先后整理出版《翁心存日记》《莫友芝日记》等清人日记,并和友人一道主编《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最近十年日记阅读和研究升温的背后,他是当之无愧的行动者。近日,本报专访张剑先生,请他谈谈历史日记的阅读及整理为何日趋升温,以及近现代日记中那些鲜活而真实的历史记忆。
>>日记成市场和研究的大“IP”
齐鲁晚报:日记之于史学的重要性,在于有别于官方的另一种历史言说。作为历史研究的“顶级资料",利用日记研究历史已然成为当前史学研究的重要途径。而我们关注到,近现代日记不仅在学术界,在出版与阅读市场已成为“宠儿”。您能介绍一下目前日记出版和研究的关注点是哪些?
张剑:一般认为,日记起源于西汉,定名于宋代,至清代达到鼎盛阶段。今天留存下来的古人日记,至少有两千种以上,但是日记在市场和学界的迅速升温,还是最近二十年的事。公私馆藏的各种日记陆续影印面世,如学苑出版社影印有《历代日记丛钞》(20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有《国家图书馆藏抄稿本日记选编》(60册)、《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86册)等;而且标点整理也蓬勃展开。
以近现代日记为例,有三大书系值得关注:一是“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此项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启动,三十余年来,陆续出版了数十种名人日记;一是《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近五年来,整理出版日记共计40余种;三是《走向世界丛书》,其中有68人81种属于日记性质。
与之相关的日记研究较前也有较大提升和拓展,首先是研究对象的范围有所扩大,原来只集中于名人日记的研究,现在连中小人物的日记也被纳入研究视野,如对山西举人刘大鹏日记的研究,就有30余篇论文,英国女学者沈艾娣还据此写了《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的专著;其次是研究视角更加丰富,以前的日记研究多集中于史料考据和政治史研究,现在还增添了环境史、地域史、生活史、疾病史、灾难史、经济史、科举史、书籍史、女性史等研究路径,观照更加立体和全面。
齐鲁晚报:20世纪初,梁启超以“新史学”为倡导,批评中国的旧史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姓之家谱,提出历史研究应重视“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与一般正史研究不同。您认为当下日记阅读和研究是否更具个性化?
张剑:人们总是通过了解他者或历史才能更加真切地认识自我和现在。但历史不仅表现为政治史,还可以表现为经济史、文化史、生活史甚至情感史。日记是一人之史,它所呈现的私人化、细节化、现场感等构成了历史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可以形成与宏大历史之间的有效互动。如果说正史提供的是一种主要由后世史官书写的、充满后见之明的宏大叙事,那么日记提供的则是一种当事人所具体感知的个体生命世界,包括大量的生活细节和丰富的情感变化,因而更具原始感和现场感,阅读起来的代入感也特别强烈。我想这是日记吸引人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阅读和研究日记,还可以适当满足一下自己的窥私愿望。
>>日记中的清末高官与末代皇帝
齐鲁晚报:具体研究中,有人感慨“时代远者,固多散佚,而时代近者,又少流传”。在浩瀚的资料选择中,您整理的日记对象如翁心存、绍英、何汝霖等多为晚清高官,为何特别关注近代史的“大人物”?
张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大人物身上所承载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相对集中、重要,二是他们的日记更多地被保存下来,更容易获得被整理的机会。但这并不是说小人物的日记就没有价值,历史有不同层面,将不同层次、不同人物的观察综合起来,才能获得对历史较为完整和客观的认识。
齐鲁晚报:作为个体生命的写照,日记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在您研究和整理的诸多日记中,哪位古人的生活细节最触动您?
张剑:翁心存的清廉!翁心存是翁同龢的父亲,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是晚清朝廷重臣。没有翁心存,很难想象翁氏会有以后的满门鼎盛的局面。现存翁心存日记,记事起于道光五年(1825),止于同治元年(1862),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日记记载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总是负债度日,即使是位居一品宰辅、体仁阁大学士后也没有改观。
如咸丰九年九月四日就记载:“房东钟氏索城寓房租甚急,重阳节近,例应催租,自古如斯,不足怪也。惟予服官四十年,无一瓦之芘,性拙于鸠,良可叹耳。”是他生活奢侈、开销巨大吗?非也。据翁同爵回忆,翁心存的朝珠从来没有用过百两银子以上的,而且即使是炎热的夏季,他连可避蚊虫的碧纱橱也舍不得添置。正是因为他仅依赖“工资”收入,又要照顾诸多亲友的生活,才导致生活如此拮据。这点,他在日记中曾有感叹:“余性拙谋生,清俸无多,……而食指浩繁,日用以此益绌。”翁心存的清廉,真是达到了衾影无愧、屋漏不惭的境界。
齐鲁晚报:通过日记研究,可以对历史的细节进行补充、完善,也可以给予修正、拓展视角。如果日记与大众熟知的历史之间出现了对立,如何进行甄别?
张剑:举个例子,就从《绍英日记》中透露的溥仪与生母自杀等信息,来看溥仪《我的前半生》的史笔和文笔。
溥仪的母亲是荣禄的女儿,与端康皇贵妃关系很好,但在有一次被端康召见后,回家就自尽了。《我的前半生》中对此的解释是:1921年9月,溥仪与端康在辞退御医范一梅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矛盾,端康盛怒之下,将溥仪的祖母和母亲都叫到宫里来,并迁怒于她们,对她们作了严厉的斥责。溥仪母亲个性极强,受不了这个刺激,从宫里回去,就吞了鸦片烟。过了一些日子,溥仪才从弟弟那里听说了母亲的死讯。
但在溥仪的“管家”之一、逊清内务府大臣绍英的日记里,却记载了溥仪当时已经从《顺天时报》中了解到母亲自尽的信息,并因而愤恨端康,甚至有“日后不认此宫”之语。溥仪母亲自尽于9月30日,10月5日的《顺天时报》第七版以《某夫人死得可怪,含冤而去,九泉下恐不瞑目》登载了此事:清室某王之夫人日前突然逝世,总统曾派荫昌吊唁致祭。乃据所闻,该夫人之死实在有些缘故,且该夫人确非因病身亡,实在是服毒而死。详细调查,与清室某贵人极有关系。某贵人年龄虽稚而位极尊,近来骄傲性成,种种行为,颇不理于人口。或云该夫人之死,因日前教调某贵人,致某贵人反唇相讥,遂一气而辞人世云。
由于溥仪“骄傲成性,种种行为,颇不理于人口”,导致其母气极服毒身亡,这种指责显然是溥仪从情感到心理都很难接受的;因此在撰写《我的前半生》时,他对某些记忆刻意回避、掩饰和做出修改,都是可能的。溥仪是因记忆修改而真的相信了自己的回忆,还是明明记得事实却故意隐讳其说,《我的前半生》为我们留下了饶有兴趣的猜想。
>>日记研究谨防碎片化
齐鲁晚报:新文化史是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一个热点,日记研究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张剑:日记文献,除少数写给“他者”看,多数具备一定的私密性、微观性,日记可以说是一种微观史和生活史。近年来中国文史学界的热点之一是关于新文化史的研究,新文化史对宏大叙事十分警惕,它喜欢考察普通民众的琐碎生活和日常世界,试图解构历史变化,做出连贯的、规律的、科学的解释。而日记的微观史和生活史性质,使其天然成为新文化史研究者非常重视和喜爱使用的史料。
但这并不是说,近年来的日记热是由新文化史引起的,只能说与其有一定关系。我一直认为是时代的发展,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时代的审美趣味,而并不是外来的某种观念。新文化史正好与我们时代的发展潮流相契合,才会合流一处滚滚向前。日记研究的兴起也是源自于内,而非自外流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排斥新文化史,恰恰相反,其积累的经验和教训足资借鉴,必须充分重视。在日记研究中,既要对新文化史呈现的多样性持欢迎态度,又要警惕其碎片化的倾向,也许只有秉持中庸之道,才是最理性的方式和选择。
齐鲁晚报:目前出版的日记按地域划分,主要集中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及北京地区,像山东等地的地方性日记,应当如何挖掘其价值?
张剑:山东是人口大省,也是文化大省。山东古人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也有不少日记。王学典、杜泽逊先生主持的《山东文献集成》中就收有一些,如韩梦周、彭以竺、丁菊甦、曹申吉、李怀民、李宪乔、丁麟年等,像李怀民、李宪乔是高密诗派的核心人物,其日记的价值可想而知。另外,还有很多山东人士日记藏于全国各大图书馆,其中不乏孤本和珍稀文献,如晚清高密秀才孙凤云的几种日记《游崂纪》《游崂续纪》《辛丁纪乱册》,就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普通古籍库。孙凤云的日记记载了崂山宫观建筑、自然风光和人文,还有捻军在当地的活动等,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值得重视。由于日记多系行草书写的手稿,因此无论是山东本地还是其他地域的日记,想要善加利用和研究,就必须先予标校整理,这也是文献学的一般规律。
新闻推荐
(本文原标题:《2018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以“创新引领时代,智慧点亮生活”为主题的2018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今天在全国范围内...
山东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山东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