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写作四十年,依然是少年
 张炜。
张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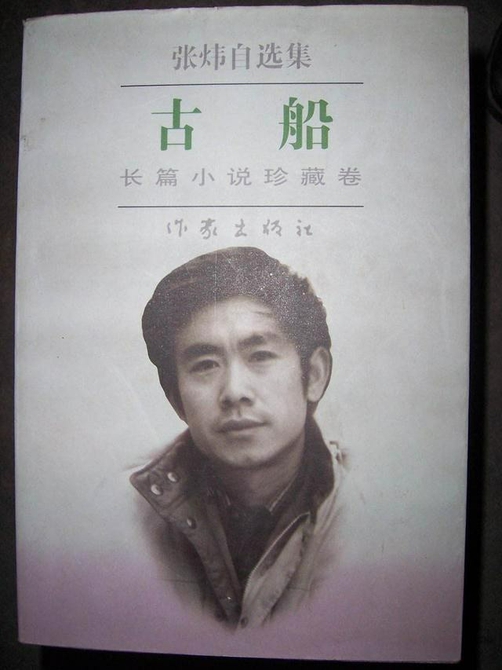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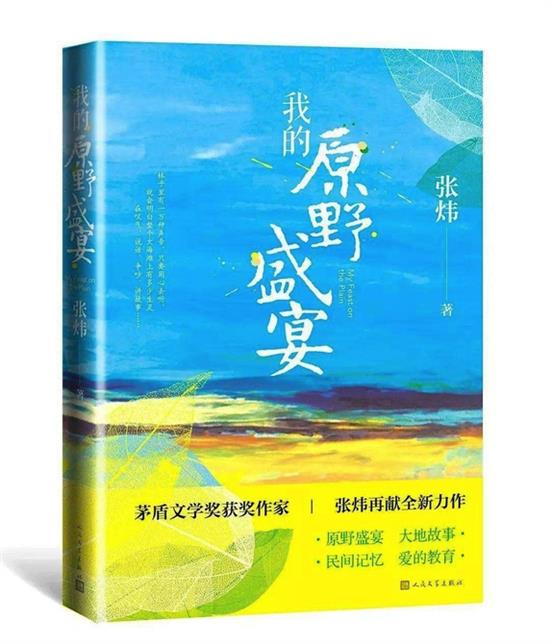 封面专访
封面专访
有不少文学作品,享有一时盛誉或者畅销至洛阳纸贵,但不一定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还有一种,隔着久远岁月重读,依然发现想完全解透它的艺术能量。张炜198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古船》,就属于后者。2019年,在人文社出版《古船》手稿本发布会上,文学评论家白烨透露,“2010年当代文学会老同志聚会,《白鹿原》《古船》《尘埃落定》是大家公认的三部长篇代表作。我跟陈忠实关系比较好,陈忠实亲自跟我说过,《古船》给了他震惊。”给过陈忠实“震惊”的《古船》,至今还留着很多待解的谜语。
与作品一起长青的还有张炜本人,虽然岁月让年龄增长,但常年在精神世界跋涉,让张炜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正如评论家李敬泽所言,“张炜依然是那个勇敢的、不怕失败的少年。”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张炜的作品是创作辨识度很强的独特存在。其作品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非常鲜明,质地却是朴素的。2002年出版《你在高原》系列,分为《家族》《橡树路》《海客谈瀛洲》《鹿眼》《忆阿雅》《我的田园》《人的杂志》《曙光与暮色》《荒原纪事》《无边的游荡》10部,为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知识分子立传。这部作品也让张炜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壹
对诗意和真理的热爱
除了长篇小说,张炜还有着丰富的儿童文学创作世界。他回到故乡,回到森林、大海和原野般非常开阔的生活当中,写出《少年与海》《寻找鱼王》等真挚明朗、精湛质朴的篇章。2020年春天,在海边林野中长大的张炜,回忆故乡的山川海滩、绿色林莽,丰饶原野、飞禽走兽,写出非虚构《我的原野盛宴》。在这部有深厚自然文学色彩的书中,张炜逼真地描绘了蒲公英、白头翁、长尾灰喜鹊、蓖麻等360多种动植物,堪称一部半岛海角动植物志。
2020年的疫情,也让人们更关注、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文学再次成为焦点。在此情况下,张炜有怎样的见解?
封面新闻:《古船》里有您自己独特的语气和节奏风格,有很强的个人辨识度。您自己对这部作品有着怎样的认知或者情感?
张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可能是写作的激越时期,起码回忆起来好像如此。那也是身心有力、向上的时期,所以才有很多认真深入的追究。对以往的事情、仿佛事不关己的东西想得很多,很激动。人处于青春岁月容易无私,而无私的精神才会感人。人上了年纪就有身体或其他方面的担心,还有长期以来经验得失的总结,所以就会变得多虑或自私一些。这当然是比较而言。相反的情形也不少见:有人老了,可是越老越公而忘私,能更勇敢地说出一些真话,为公众和社会争利益。这样的老人真是纯洁,是青春永在的人。
封面新闻:在《古船》后记中,您写道,“自己这十年来的写作尚为努力,几乎是全力以赴的、自谦自信和永不满足的。我不敢荒废光阴,不曾停止学习,更没有沾沾自喜;我一直把创作当成心灵的至高要求,同时又化为不间断的劳作。”这么多年来我相信您还是一直如此。这种努力给您带来了怎样的馈赠?
张炜:一个人的努力工作或说劳动,是一种乐趣相随的辛苦。在较长较大的工作任务和目标面前,眼睛望过去会感到畏惧,但只要从头干起来就好了,诸多困难也会迎刃而解。所以劳动者总是对自己的双手感到满意。他对长期以来的劳动积累下的数量并不敏感,而只对这个过程有更多感受和享受。劳动者的主要收获或馈赠,尽在于此。如果写过了四十年或更长一点,工作对他意味着什么,大概总会明白一些了。
封面新闻:您的小说也具有散文化特征。不是那种很突出的戏剧化情节化小说。这背后连着您怎样的艺术美学追求?
张炜:我对最好的虚构类文字还是十分着迷的,不过这种作品在书店里很少。为数不少的虑构都是胡编乱造,不属于语言艺术,看它们是白白浪费时间。我会更多地去找那些非虚构作品看,比如一些有意思的历史人物的一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所谓的非虚构也是相对的,这些书也不可能没有作者的私货夹带其中。不过总的来说,还是比开门见山就说自己是虚构的那些文字要可靠一些。没有比编造糟烂故事给人看再无聊的事情了。杰出的虚构故事一定是隐下了最大的真实,这都是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的。另外,这一类绝妙的语言艺术也不是其他体裁所能取代的。可惜这样的杰作很难见到,轻浮草率的编造太多。如果写出那样廉价的虚构文字,写作者将羞愧。我严格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贰
尽可能不去浪费光阴
在文学创作之外,张炜也在古典文学的读解上深耕细作。他以二十余年之功,阅读并阐发经典,著成《张炜读解古典文学专著系列(四卷本)》。该系列包括《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增订本)和《读〈诗经〉》四本,第五本《读解苏东坡》正在筹备当中。
封面新闻:您对李白“天才”的解释,非常独特。现在诠释传统人物者众,如何不落俗套,挖掘出新意来,您有怎样的心得?
张炜:古代的诗人和学者,他们有自己需要面对的现实,有自己的心情。读他们是一个感动和感慨的过程,只要读进去,就会这样。我读到后来人,特别是现代人写下关于他们的文字,心里常有遗憾泛起。后来人常常过多地从我们现在的生活出发去要求他们、理解他们,有时到了蛮不讲理的地步。还想让他们努力地、公开地去反对皇帝和孔子等,这也是不替古人考虑,只为自己时下生存考虑,透出自私或天真无知。那时的人尽管离开了我们几千年或几百年,作为人的心理及人性的特征,与今天的人并无大的不同,他们面对不平,苦难,利益,权利,胁迫,疾病,饥饿种种情况,做出的反应大致和现在的人一样。如果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就要格外重视了,因为这一定是有重要的原因在里面,弄清这些原因才是极有意义的。比如一个古人突然极其勇敢,能够直接痛斥权贵;比如一个人快被处死了还能作出文采丰沛的诗文;比如一口气喝掉无数美酒后还能呼号欢歌者。这种种情形都异于常人,所以就需要从头、从深处找出缘由。这些寻找的过程,是认识生活与人、更是认识时代的大路径。
封面新闻:人在这世界上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不易。您是如何处理或者面对的?
张炜:是的,人生多艰,会不断地被绝望缠住,被不幸和哀伤攫住,但生活总要继续下去,写作也就继续下去。对自己工作持守的标准和原则,哪怕是最基本的,也有可能是很难的。怎样对待文学这种好像“可有可无”的事业,这是一个问题。“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笔下的王子提出了这样惊心的命题,其实也关涉到文学。我是这样看待文学的,所以尽可能不去浪费光阴,努力坚持诚实和干净的工作。这样度过时间,是对生存的安慰。现在我写出的文字,和第一部长篇的质地一样,一直在那样的状态中。叁
要更审慎对待这个世界
封面新闻:现在这个时代,文学要获得读者,很不容易。因为大众拥有多元化的信息获取方式、精神娱乐平台、文化消费方式。那么在您看来,除了大众自己要觉醒,作为文学创作者的作家,应该如何努力?
张炜:这真是个严肃到极点的问题。追随时尚,在流行和习惯中顺水漂流,不知不觉就抵达了生命的站点,这样似乎高高兴兴一场下来,也没什么不好。这种并无脾气的和顺老好人是从来不缺的,可是如果都做这样的老好人,我们的世界将一塌糊涂。不,我们要更审慎地对待这个世界,沉思和鉴别,动笔三思。在这个芜杂的网络中,要有重金属的响声。它落下来,被淹没;再落下来,再被淹没。可是一直落下来,就有意义。好的文学之页中一定有一颗非同一般的心灵,这个心灵由于一直诗意盎然追求真理,最终会像出于污泥的莲花一样。我们一起爱护它,培植它,栽种它。我们也想成为它。用一支笔,努力认真地刻下每一个字。真正的阅读者是存在的。我们只为明晰冷观的眼睛写下这一切,留下自己的劳动。
封面新闻:您的作品里充满对大自然各种生命的热爱。最近疫情暴发,让很多人思考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微生物的关系。
张炜:有的地方,有人看到一个动物,哪怕根本就不认识它,哪怕它长得楚楚动人可爱之极,有人首先想到的竟然是怎样吃掉它、它的味道如何以及烹饪的方法。可见这样的人并非是因为饥饿,不仅是怪癖,而直接就是一种嗜杀的恶性。这样的人不配享有安全的生活,也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我们的最大问题是,目前仍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这种恶性附身没有警惕,尚且与之共处。因此,一旦灾难性的报复加到身上,也就不必抱怨。人类离幸福和谐的道路还很漫长。这需要有一个指标,即看人类与自然、与其他一切生灵如何相处。如果人类将另一方的被杀戮被损害作为生存的前提,也就不会获得安宁,报复将以各种形式落到我们身上。人类在地球上的各种屠宰场不能归零,苦难也就不会归零。
封面新闻: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您是怎样的状态?
张炜:人类获得的物质积累是很容易失去的,原来一切是这样脆弱。在斗室中,我们更多地面对人类的精神积累即书籍,会有阵阵惊讶。我们不知道人类在漫长的灾变历史上,会有这样坚韧不屈的守望、这么天真烂漫的想象,以及这么多的顽皮。他们记下了各种各样的情感、事件、美和丑。一些荒诞不经的嬉戏,还有糟糕的沉沦、荒淫无耻,令人觉得是绝望的间隙。在这样的日子里,写作者会不自觉地想象和揣测未来的劳动,其意义的变化、道路的选择、内容的展现,更有勇气和责任、生存方式这许多思忖。文字的记录的确是不可取代的,即便发明了视频录像这类方法,文字的力量还是以强大的特征表现出来。文字伴随了更大的自由,让深沉的灵魂隐匿其中。所以,让我们再选择一次,还是会选择文字。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新闻推荐
【报告摘要】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