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短情长见信如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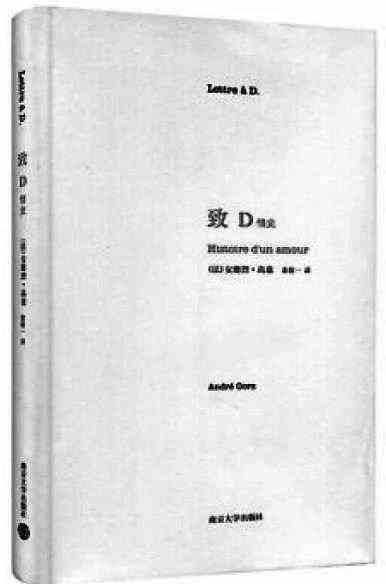
书信,因其私密性、个人化的特质,是对一个人经历、情感、想法的真实体现,一个人的文字也往往会在原有的风格中,显现溢出创作常态的有趣变化。相对比其他沟通方式,一个人的心性与见地、感情与追求,往往都会在信件中袒露得更彻底、更亲切,也正是如此,我们才更容易被触动,被折服。归根结底,信是载体,传递的是情。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读读那些饱含深情的信件,感受下其中流露出的款款深情。
人间“苦茶”终遇糖
说起民国著名的情书王子,沈从文、徐志摩肯定当仁不让。试想一下怒目圆睁、正襟危坐的冷面先生,让人不寒而栗、避之不及的冷面斗士说起情话来,是不是更具有反差萌。
1925年,鲁迅在北大与女师大做兼职教师,时年45岁。3月11日,他收到了一封女大学生的来信。写信人叫许广平,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女生,这一年26岁。她给鲁迅先生写信,是为了探讨革除学校制度流弊以及国家教育的未来。收到许广平来信的当天,鲁迅便以“广平兄”相称,给她写了封回信。正是这封谈学风论政治、言人生说处世的回信,开启了此后两个人的一世情缘。从此,鲁迅这杯人间“苦茶”,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糖”。
许多年之后,回忆起自己与鲁迅初见,许广平这样说:“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重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我们印象中的鲁迅。鲁迅的随笔杂文犀利冷峻,但是他的家书却温暖细腻。《两地书》中,收录了鲁迅和许广平4年间100多封通信,真可谓是两地书,一世情。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我寄给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我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是疑心那里会慢一点。天天寄同一名字的信,邮局的人会不会觉得古怪?”
“我不知乖姑睡了没有?我觉得她一定还未睡着,以为我正在大谈三年来的经历了。其实并未大谈,我现在只望乖姑要乖,保养自己,我也当平心和气,度过预定的时光,不使小刺猬忧虑。今天就是这样吧,下回再谈。”(乖姑、小刺猬都是许广平的昵称)
鲁迅在厦门任教,许广平为鲁迅寄去的衣服,回信:“包裹已经取来了,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这样就可以过冬,无需棉袍了;此地冷了几天,但夹袍亦已够,大约穿背心而无棉袍,足可过冬了。”
班里来了几个女同学,鲁迅也第一时间汇报:“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
就像鲁迅自己评价《两地书》:一本书,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如果定要恭维这一本书的特色,那么,我想,恐怕是因为它的平凡罢。在他看来,这些信件就是最日常的对话,是最平凡的纪念。
我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
308封情书,封封感人肺腑,句句动人心魄,字字刻骨铭心!1932年秋,朱生豪在之江大学与宋清如相识,两人志趣相投,相知相许。1933年,朱生豪毕业后,两人两地分隔,开始近十年的苦恋之旅,以书信交流情感,倾诉相思。从1933年到1942年两人结婚,到1944年朱生豪去世,这些情书见证了传奇而悲壮的爱情。正是由于伟大的爱情和患难与共的知己,才成就了一代译莎巨匠。
无论是讲道理、诉真情、论诗作、品电影,字里行间都充满宠溺,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题。聊理想、谈人生、诉爱情、倾泻喜怒哀乐,读书、品电影、交流诗作、切磋译事……贯穿始终的主线是对宋清如无限的思念和爱慕。
朱生豪在现实中本是一个内向寡言之人,唯有给清如的书信,笔下俏皮生花。滔滔不绝,俏皮、苦恼、纠结、幽默等跃然纸上,洋溢着浓郁的青春气息。
朱生豪把纯美的爱情献给了宋清如,把生命献给了莎士比亚戏剧。有人曾评价,朱生豪在32年的人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翻译31部半莎翁戏剧,二是爱上宋清如。也有人说,她遇上他,是她生命中重要的大事。
光是给爱人起的爱称,就多得肉麻得让人欣羡不已。例如“澄、宋儿、阿宋、青女、宋神经、小鬼头儿、清如仁姐大人”。
女人都会担心容颜老去,他却说,“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上帝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
偶尔朱生豪也有霸道总裁式的酥语,“要是世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多么好,我一定要把你欺负得哭不出来。”
这里一切都是丑的,风、雨、太阳,都丑,人也丑,我也丑得很。只有你是青天一样可羡。
明天,明天,明天,明天该是这半月来最长的一天,要是你不来,那一切都完了。
我是,我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
希望你快快地爱上一个人,让那个人欺负你,如同你欺负我一样。
我一天一天明白你的平凡,同时却一天一天更深切地爱你。你如同照镜子,你不会看得见你特别好的所在,但你如走进我的心里来时,你一定能知道自己是怎样好法……
我们都是世上多余的人,但至少我们对于彼此都是世界最重要的人。
我想作诗,写雨,写夜的相思,写你,写不出。
我想要在茅亭里看雨、假山边看蚂蚁,看蝴蝶恋爱,看蜘蛛结网,看水,看船,看云,看瀑布,看宋清如甜甜地睡觉。
来生仍与你同行
《致D情史》的作者是安德烈·高兹,一个法国哲学家,与萨特交好。他在哲学上的成就不大,其名声远不及同时代的萨特、加缪等人,他最让世人铭记的,不是其哲学作品,而是这本号称给多莉娜(Dorine)的“爱情墓志铭”。这本书其实只有这一封情书,在书中,他回溯了两个人相爱相知相伴一生的点滴,在写下这封情书的第二年,因为不愿意在对方死后孤独地生活,他和身患绝症的妻子双双自杀,共赴黄泉。
《致D情史》因此也就成了绝唱,这本纯粹记述两人感情经历的爱情告白,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安德烈曾经写过的任何一部著作。
“和你在一起我才明白,欢愉不是得到或者给予。只有在互相给予,并且能够唤起另一方赠与的愿望时,欢愉才能存在。”
“如果你和一个人结合在一起,打算度过一生,就将你们两个人的生命放在一起,不要做有损你们结合的事。构建你们的夫妻关系就是你们共同的计划,你们永远都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加强、改变,重新调整方向。你们怎么做,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致D情史》的最后一段话没有华丽的语言,只有真真切切地担心失去对方的恐惧和深情。这是一封跨越时间、跨越生死的情书,浓烈热情,掷地有声——
“很快你就八十二岁了。身高缩短了六厘米,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幽雅,令我心动。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五十八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我们经常对彼此说,万一有来生,我们仍然愿意共同度过。”
云中谁寄锦书来
1949年的纽约,曼哈顿一间没有暖气的公寓里,三十三岁的穷作家海莲,偶然看到一则伦敦旧书店的广告,凭着一股莽撞劲,她开始给这个伦敦地址写信。这一写,就写了二十年。而那家书店的地址——查令十字街84号,已经成为全球爱书人之间的一个暗号。三十多年来,人们读它、写它、演它,在这段传奇里彼此问候,相互取暖。
海莲和弗兰克他们之间,慢慢地,有了像亲人一样的情感。他们有时在闲话家常,但大多时候,是在谈书。海莲来信幽默风趣,弗兰克回信绅士有风度,从来未曾见过面的两人,在信件的往来中达到了灵魂上的高度契合。
在整本书中,最令我动容的两点是,以书为载体的心灵交流,和以信为形式的丰富情感。他们的对话看起来似乎很没有效率,娓娓道来,慢悠悠地说那么几句,聊聊彼此的生活,但是却能够直抵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让读的人心里一颤——
我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看到你们刊登的广告,上头说你们“专营绝版书”。另一个字眼“古书商”总是令我望之却步,因为我老是认为:既然“古”,一定也很“贵”吧。而我只不过是一名对书籍有着“古老”胃口的穷作家罢了。在我住的地方,总买不到我想读的书,要不是索价奇昂的珍本,就是巴诺书店里头那些被小鬼们涂得乱七八糟的邋遢书。随信附上一份清单,上面列出我目前最想读而又遍寻不着的几本书。如果贵店有符合该书单所列,而每本又不高于五美元的话,可否径将此函视为订购单,并将书寄给我?
你忠实的海莲·汉芙(小姐)
晨报记者 侯梦梦
新闻推荐
■彭忠富法国《世界报》曾评论道,“余华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的巴尔扎克。”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巴尔扎克塑造的葛朗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