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中遗物》 将惊悚故事作为记忆的窗口
 玛丽安娜·恩里克斯
玛丽安娜·恩里克斯
阿根廷作家,记者。1973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95年凭借处女作《堕落最糟糕》(Bajar es lo peor)在西班牙语文坛崭露头角,其后又发表了多部小说和短篇小说集,跻身拉美重要作家之列,被誉为“惊悚小说公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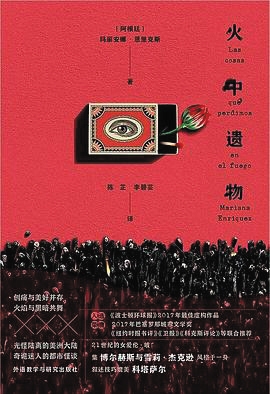 《火中遗物》
《火中遗物》
作者:(阿根廷)玛丽安娜·恩里克斯
译者:陈芷、李碧芸
版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年4月
阿根廷作家恩里克斯的小说《火中遗物》收录了12个颇具黑暗魔幻风格的短篇故事。这种浓烈的拉美文学风格或许会让人们再次陷入其中的魔幻,而忽略文本背后所指涉的现实问题。
惊悚与魔幻的刻板表象
耶鲁大学研究西班牙语文学的著名学者罗伯托·冈萨雷斯曾指出,拉美历史之于拉美叙事文学,正如史诗主题之于西班牙文学,换言之,在拉美小说中,本地的历史是永恒的主题,出现方式可以变换,但几乎从不缺席。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在认识拉美文学的过程中“祛魅”——祛“魔幻”之魅。在中文翻译的世界文学市场上,拉美文学往往被刻意地贴上“魔幻”的招牌,仿佛这道招牌是再创马尔克斯或博尔赫斯作品销售奇迹的保证。“魔幻”的包装,一方面会制造一种关于拉美文学的刻板印象,遮蔽那些不以魔幻元素见长的拉美文学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很多时候也是对作家的背叛,因为他们的意图远不只是以“魔幻”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而已,他们想表现更多的东西——比如,本国的历史,被官方话语矫饰、歪曲或者删除的历史事实。
出生于1973年的阿根廷作家玛丽安娜·恩里克斯创作的这本短篇小说集《火中遗物》,若是完全抛开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来读,很适合喜欢看鬼片、悬疑片、惊悚片的读者,从叙事节奏、画面感的营造来看,作者很有可能也对这类影视作品有所借鉴。对于了解阿根廷历史,特别是1976年至1983年军人独裁时期历史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则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如果我们把心理现实也当成现实之一种的话。那个年代发生的种种惨案经过私下转述而留存脑海中的个人记忆、对随时有可能降临在自己头上的暴力的恐惧、国家持续动荡在国民心头造成的难以平复的不安感……凡此种种,拧成心结,变为噩梦,再现于文学或艺术作品中。
黑暗风格与噩梦的由来
两个女孩在月黑风高之夜偷偷潜入一个据说曾经做过警察学校的旅店,想完成一个恶作剧式的报复计划,却亲眼看到多年以前在此地发生的暴行如电影般重现,她们被吓得精神崩溃,向大人们讲述自己看到的恐怖场景,而所有人都认为她们是在撒谎。这是《火中遗物》里的一个故事。细细想来,这两个女孩是未曾亲历那个恐怖年代的,她们是不小心在时光隧道里走了一遭,还是在恶作剧之余躺下休息时做了同一个噩梦?为这个噩梦提供素材的,是不是她们从大人那里听来的传说?曾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阿根廷电影《谜一样的双眼》中,有个镜头我印象颇深:那个恐怖年代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有一天夜里,男主人公做噩梦,在迷迷糊糊中拿起笔在便签纸上写了一个词:TEMO(我害怕)。阿根廷民主化之后,大多数在军政府大搞国家恐怖主义时期犯下暴行的人被免于责罚,仿佛阿根廷从未发生过那些残暴之事。对于恐怖年代的幸存者们来说,在悲愤之余,不堪回首的过往是时时在夜里袭来的梦魇。
在《火中遗物》的另一个故事里,一个女孩在路边捡到了一个骷髅头,竟视之为情同姐妹的伴侣,为了补全它,找到它缺失的骨头,就跑到一个公用墓穴那里去挖掘那些被“抛弃”、被“遗忘”的骨头。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公用墓穴就是当年用来掩埋被军人独裁政府非法杀害的异见人士的尸体的,他们在官方话语里成了“失踪者”,事实上,他们变成了深埋地底的被抛弃、被遗忘的白骨。
这些失踪者在阿根廷当代文学中复活。在里卡多·皮格利亚、吉列尔莫·马丁内斯、路易莎·巴伦苏埃拉、玛蒂尔德·桑切斯等人的虚构故事中,浮现着失踪者们的血肉之躯或神秘幻影。这些失踪者可以被认为构成了阿根廷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吗?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以“虚空”(ausencia)的理念将失踪者主题、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博尔赫斯连通起来。在他看来,作为阿根廷文学首要生产地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座以虚空为特色的城市:位于潘帕斯的茫茫原野和大西洋的浩渺烟波之间,它在虚空中呐喊,抱怨自己对欧洲的模仿总是不够彻底,总是那么缺乏“文明”气息,于是,博尔赫斯用他虚造的特隆、乌克巴尔和奥比斯·特蒂乌斯来填补布城的虚空,比奥伊·卡萨雷斯用《莫雷尔的发明》里的怪诞机器来表现虚空,然后虚空又演化为军政府统治时期不计其数的失踪谜案,那些半夜被人抓去、自此杳无音讯的布城市民……
现代文明背后的蛮荒之地
我更倾向于用“野蛮”(barbarie)或者“蛮荒”(salvajismo)来取代“虚空”,作为解读阿根廷文学的一把钥匙,不过光有这把钥匙还不够,还需另一把叫做“文明”(civilización)的钥匙。阿根廷的一面是拉丁美洲最具现代气息的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一面是布城之外的蛮荒原野、欠发达内陆;一面是短暂的经济繁荣许诺的全面现代化的美好理想,一面是历史倒退、暴力横行的惨淡现实。在阿根廷文学中,一面是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等一众大师堪与欧美一流作家比肩的美学意识和叙事手法,是可以被视为现代文明丰硕果实的文学现代性,另一面则是那些屡见不鲜的与暴力、犯罪、野蛮挂钩的文学题材:居无定所、喜欢舞刀斗狠的高乔人、受大男子主义情结驱使对女伴痛下杀手的罪犯……以及历届独裁者执政时期发生的种种血腥惨案。
构成《火中遗物》的12个小故事,时时散发出蛮荒的气息。一对夫妇从首都开车前往内陆,见识了一个与布城截然不同的丛林世界,那个对阿根廷的“落后”地区极度不适应的丈夫最终神秘失踪,这令人联想起奥拉西奥·基罗加的一些作品,作为西语美洲短篇小说的先驱者,基罗加深入阿根廷北部丛林地区,讲述大自然的神秘力量把人吞噬的惊悚故事。在《火中遗物》这个作为题眼的故事里,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神秘组织在旷野上举行类似宗教裁判所火刑的残酷仪式,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现场拍摄的视频,以此抗议在阿根廷不断发生的性别暴力事件,用自虐的暴力来对抗男性对女性施加的习以为常的暴力。这些蛮荒故事的讲述口吻总带着一点黑色幽默的意味,使得我们在阅读时不致心情过于沉重。如果抗议家暴、选择自焚从而毁容的女人越来越多,那么“男人和女怪物组成的完美世界何时到来?”这样的反乌托邦话语看似荒诞可笑,实则发出了严厉的社会批判。
《中毒的岁月》这个故事则让人笑不起来,叙述者描绘了1989年至1994年自己的成长经历,家里的生活质量每况愈下,从中产家庭沦为贫民家庭,这位丧失了希望的女孩学会了酗酒、吸毒、荒废学业,让自己成为欲望和毒瘾的奴隶,成为一个没有梦想、只有致幻剂带来的噩梦的野蛮人。作者没有说的是,在这个最终走向暴力犯罪的少女的野蛮背后,是更大的野蛮:在卡洛斯·梅内姆担任阿根廷总统期间,一群衣冠楚楚的强盗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之名掠夺公共资源,把老百姓的财富扒得底裤都不剩。对于大多数阿根廷人来说,这也是回顾时免不了悲伤和愤怒的历史记忆。
这12个小故事的主人公或叙事者多是女性。那种比较狭隘的文学理论往往强调女性作家书写私密内心的优势而忽略其他,仿佛女作家只会写内心活动、姐妹情深,只会写女性读者爱看的文字。《火中遗物》的作者玛丽安娜·恩里克斯就在一次访谈中坦承,她极为厌恶那种把女性文学看成是专门表达私密内心的文学的说法,这种说法将女性作家的创作框定在琐碎之事、细微情感或是身体主题的角落里;她认为女作家应当大胆尝试那些被认为不适合女性创作的体裁——不要忘了,创造出“弗兰肯斯坦”这个怪物的,正是一个女作家,而《弗兰肯斯坦》绝不是什么表现内心世界的小说。作为一个喜欢看悬疑片、惊悚片的男性读者,我认为《火中遗物》给我带来了蛮过瘾的欣赏体验,至于作者是男是女,我觉得无关紧要。
□张伟劼
新闻推荐
李洱文学报文学课看完作家李洱《应物兄》的读者,会对他的阅读经历产生浓厚兴趣。他曾比喻说,“在写作的时刻,会一分为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