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夏邦:《月光狂想曲》是披着家族史外衣的小说
有一些回忆是死亡触发的:人们在临终前吐露的秘密,整理遗物时发现的日记本,清明时在墓前想起的一道菜,旧书里掉落出的一片树叶。
一个叫迈克尔·夏邦的美国小说家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的外公在诊断出骨癌后,一改往日的沉默,开始向迈克尔讲述自己的生平。从年轻时盛怒之下将一只猫扔出窗外,到二战时随军前往德国,奉命寻找火箭专家冯·布劳恩,再到丧妻后在养老院的一段短暂恋情,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不同年代的故事像不同颜色与质地的碎布头,需要动用全部的感性与智慧,才能将它们缝成一床百家被。历经沧桑的外公原本对讲述的力量不抱希望。他轻蔑地问迈克尔,你觉得这解释了一切?不过是些名字、日期和地点而已。小说家却不这么认为,在病床前,他怂恿外公讲下去,讲下去,因为他相信“秘密就像肿瘤,叙述则是明亮灼热的放射线,用照射给予治愈”。
只不过,这一切从未发生过。在历史上,外公从未在德国丛林里找到火箭,从未因杀人未遂而坐牢,从未有过一个美丽动人却因二战经历而患有精神疾病的妻子。《月光狂想曲》是一本披着回忆录外衣的小说,一部在“作者注”里与读者签下契约的虚构作品,一个不仅关乎历史、更关乎人们如何讲述历史的故事。通过扎实的细节、出色的结构掌控、对黑白照片动情的凝视,迈克尔·夏邦将一个有着“灰色的海洋、灰色的金发、灰色的番茄酱”的世界唤醒,一点一点恢复了它们本来的颜色。
 迈克尔·夏邦
迈克尔·夏邦
迈克尔·夏邦是近几年最受瞩目的美国作家,他既摘取过文学性很强的普利策小说奖,也获得过颁给幻想题材的星云奖和雨果奖,还曾出任好莱坞电影《蝙蝠侠》和《异星战场》的编剧。最近,澎湃新闻对住在加州的迈克尔·夏邦进行了采访。
在家庭内部构筑起了历史
澎湃新闻:让我们从作者注聊起吧。“在准备这本回忆录的过程中,我尽量以事实为根据,除非事实与我的记忆、叙事目的或我所理解的现实相冲突。”
夏邦:这也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说法承认:我在撒谎。
澎湃新闻:的确。我们也知道有一些非虚构作者并非恪守事实,这句话是否也是一种暗讽?
夏邦: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不过是不是暗讽,我不好说。作为小说家,作为一个毕生写小说的人,也就是说,一个试图给随机、无序的材料和经历赋予形状和意义、并坦荡承认这一点的人,看到文学回忆录获得越来越高的地位和声望,让我有些担心。人们阅读回忆录,因为它赋予他们的混沌经历以形状、秩序和图案。但这样做本来就是在虚构。我并不是在批评虚构这一行为,我认为这是我们人类的大脑完成的最动人的事。某种程度上,在无序中寻找秩序让我们得以存活。但是如果进行了虚构却并不承认这一点,这让我很忧心。但我忧心的不是说回忆录作家这么做,我认为绝大多数回忆录作家都在真诚地、尽可能准确地记下他们记得的经历,真正让我忧心的是读者们,他们过于轻信、不假思索地接受读到的一切,他们对非虚构作品过分信任、并且认为它们高于小说,殊不知小说其实做的就是非虚构作品做的事,只不过更公开,甚至在我看来,完成得更出色,因为回忆录总是会被贴紧事实的规则所束缚。
澎湃新闻:美国纪实频道如今已被真人秀占据。我们似乎对现实有一种饥渴。
夏邦:我觉得我们在渴求意义和知识,渴求一种人生是有序的安心感。我们希望历史是有秩序的,在历史中能获得意义;宗教也是另外一种在虚无中寻找意义的方式。
澎湃新闻:《月光狂想曲》探索了历史的呈现,以及历史的不可获得。从大屠杀后对可怖图像传播的禁止,到受害者因精神疾病而无法言说自身经历,似乎有太多因素阻止个人记忆向下一代传递。这是不是促使你书写这一主题的原因?
夏邦:我刚开始写时并没想到这一点。小说主要围绕着家族史展开,关注家庭是如何创造历史的。什么留下来了,什么被漏掉了,我们能知道些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我写作的出发点。我的灵感是我从外公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说他的兄弟被公司辞退了,只因为要给阿尔杰·西斯腾出位子。在试图展开这段轶闻时,我迅速把叔公改成了外公,因为谁会写一本关于他叔公的小说啊?写外公感觉更为亲切。当我开始有意识地展开虚构后,我仍然保留了那种回忆家族往事的口吻。
几天后,我去问我的堂姐妹,也就是我的杰克叔公的女儿,弗朗西斯,还有她的女儿杰西卡,杰西卡和我是同龄人,我们关系很好。我给她们两人写邮件:你们还记得杰克叔公因为阿尔杰·西斯而被解雇的事吗?杰西卡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件事。弗朗西斯回复我说,我听到的版本不是这样的。我听到的是我父亲从来没有被炒鱿鱼,他只是有一天下班回家,说他简直不敢相信A也在他们公司卖纸张产品。于是我又问我母亲,你知道这事吗?她说,对啊,他因为阿尔杰被炒了。她是从我外公那里听来的。那么,我们要怎么知道真相呢?我外公已经去世多年,阿尔杰也去世很久了。我们再也没有办法获知真相。我就是在这时意识到自己的主题,我在写家族史。
当我开始动笔,外公开始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后,我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更大的主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冯·布劳恩。你的问题是在传播中被遗漏的历史,冯·布劳恩的历史就是被人为地阻断了。当他在战后定居美国后,他的过去被抹掉了,他的纳粹档案被清空,然后他才得以进行研究,尽管人人都知道是他发明了V2火箭这一纳粹致命武器。他说他是被逼的,是被迫加入纳粹的,而整个社会相信了他,因为政府希望我们这么相信,于是任何戳穿他谎言的证据都被删除了。冯·布劳恩的官方档案就这样成了“真相”,直到他人生最后几年,一些幸存者开始出版回忆录,真相才浮出水面,但冯·布劳恩从未承认。对我来说,写小说是由许多偶然组成。下笔前我根本想不到究竟发生了什么,完全出乎预料,当我开始写我虚构的外公被解雇时,我根本想不到我会写到冯·布劳恩或者V2火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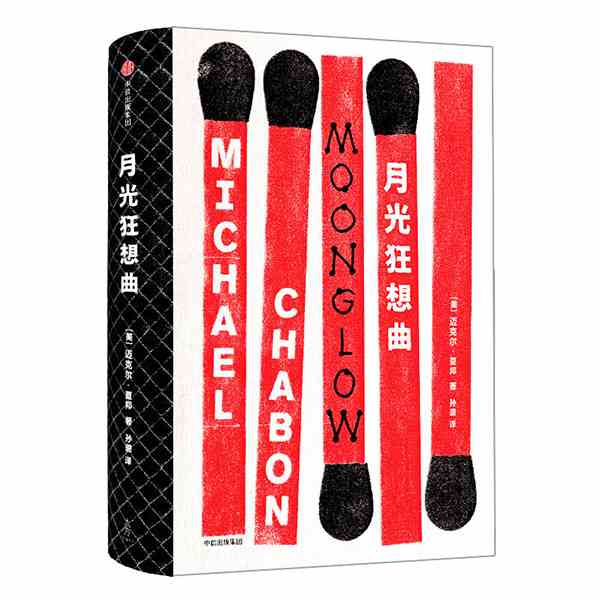 《月光狂想曲》书封。
《月光狂想曲》书封。
澎湃新闻:这大概就是写小说的乐趣,不是去写你知道的,而是写你不知道的。
夏邦:对,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开始总是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大纲,然后一路摸索发现,这也是我为什么写一部小说要花这么久,因为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在死胡同里转,以为它能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有的时候我会浪费一两年的时间,最后写的全部不行,只有扔掉,从头再来。这种写法非常低效,要是我知道我会去那儿我的效率会高得多,但我只会这么写。如果我知道我要写什么,那么就失去写小说的意义了。
写《月光狂想曲》时,我没有走很大的弯路。我想部分原因是我可以在时间线上跳跃,这本书的结构就是如此。当我陷入瓶颈,我就跳到另一个时间,写另一段时间发生的事,这通常能帮助我解决另外一部分故事的问题。但在写《犹太警察工会》时,我写了600页的草稿,最后几乎全部舍弃了。
澎湃新闻:我个人很喜欢这本小说的一点,是它提供了很多进入过去的通道:玩具、扑克牌、香水瓶、太空模型。你是有意想通过个人的物什来调度私人史,从而搭建一个迷你博物馆吗?
夏邦:我并不是有意为之,但听你一说,我觉得很有道理。我觉得我这么写大概是因为我们是通过物件、传家宝、破烂、箱底货……这些我们不知为何舍不得扔的东西,这些我们一度丢失又重新收获的东西,在家庭内部构筑起了历史。
“冷战全方位地影响了我的经历”
澎湃新闻:2017年的电影业迎来了两部讲述二战的电影,《敦刻尔克》和《至暗时刻》。你觉得这是人们对二战重新燃起兴趣了吗?
夏邦:你可以说是一种复兴,但其实它并没有真正走开。我生长于六七十年代,那时关于二战的故事俯拾皆是,电视上、电影里、喜剧片、情节片、漫画书,它占领了各种大众媒体。我们有一张关于二战的全方位的地图,我认为现在真正消失了的是那些劣质的、烂俗的二战叙事,它们消失了。我想大概总体来说社会文化对二战的关注会随着时间淡去,但取而代之的会是更高质量的文学影视作品。
澎湃新闻:在这个文本丰富的二战文学传统里写作,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
夏邦:有不少挑战。其中一个是我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二战,而我们已经有了很多二战经历者写下的出色小说,这会让我畏手畏脚,但同时也可以将其视作挑战,鞭笞我做足功课,用研究和想象力来弥补个人经验的缺失。另一个挑战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多伟大的作品,后来者很难找到还未挖掘过的题材。第一梯队的作家写了显而易见的素材,第二梯队的写了不那么显而易见的,第三梯队写了更不容易发现的,现在再来寻找角度就更难了。在写《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时,我让我的人物角色经历二战,我要想该怎么去写,人物要怎么行动,如何与文学传统中已有的作品进行竞争,如何超越它们、或如何以有价值的方式与它们区分开来。我最后干脆发明了一个舞台,我让他们去南极,我假装那里有一个美国的军事观测站,还有一个德国的观测站,故事最终以一种悲喜剧的方式告终,这是我找到的一个具体方案。
还有一个挑战是如何写大屠杀,那么写作者要面对“贩卖悲情”这个问题,我不想将大屠杀用作一个煽情的道具或噱头。我非常有意识地避免过度消费大屠杀,而我的做法通常是以非直接的方式处理它,要么让它发生在幕后,或非直接地将它引入故事。
澎湃新闻:比如外婆的故事。我们并不知道她的二战经历,只是看到她战后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
夏邦:没错。
澎湃新闻:这本小说还有很大一部分在讲冷战,尤其是冷战期间的美苏太空竞赛。在冷战下成长对你的思考和写作有影响吗?
夏邦:直到苏联解体,冷战是我整段童年的决定性因素。它全方位地影响了我的经历,决定了我看的电视,读的小说和非虚构,我看的新闻,比如越战。整个童年时代我都在担心核战争、美苏交锋。尤其是在里根在职早期,他和苏联政府态度都很强硬,我每天晚上入睡时都会想我第二天早上不会醒过来了,整个世界随时都会终结。冷战的影响非常之深,回到你上一个问题,理解冷战很大程度上要求我们去了解二战,去明白冷战其实是二战的下半场,主要参战国家相同,布阵和作战方式不同,冷战的许多议题、意识形态、战略都直接来自参战国家在二战时的经历。因此尽管我没有亲身经历二战,但我在冷战中成长的经历和二战历史有一种无缝衔接的感觉。
澎湃新闻:听到伊隆·马斯克的“猎鹰”火箭成功发射的消息,你的心情如何?
夏邦:我很激动。太空竞争是冷战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我伴随着太空项目的发展而长大,但我知道我们有能力超越琐碎的国与国的竞争。我从电视剧《星际迷航》和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感受到一种愿景、一个蓝图。我深深地、深深地相信它。当我关注伊隆·马斯克发射“猎鹰”的新闻时,他在访谈中有意强调了这种超越冷战视野的太空旅行精神,这种我们作为人类的求知探索,宏大的乐观主义精神。
澎湃新闻:书中尼克尔神父和外公关于月亮和太空的对话让我印象深刻。能谈谈你是怎么写出那一段的吗?
夏邦:我想一想。我开始写那一章时,外公和战友入了城,他想找冯·布劳恩,然后他们遇到了一场巷战,一个人朝他们射击,那个人后来死了。然后那个牧师就上场了。他一出来,我就得回答一些问题:他在这里干嘛?我怎么让他的存在变得合理?我喜欢这个想法,我为它感到激动,于是我发现神父是一个业余天文爱好者,他毕生都在观察月亮,他也梦想着探索太空。或许这是我对外公的一种慈悲:我让他沉迷于这个幻想中的冯·布劳恩,他非常孤独,渴望有个朋友,他交的唯一一个朋友战死了,他很脆弱,他寻找冯·布劳恩,以为后者会成为他的朋友,我替他感到难过,因为他想象中的冯·布劳恩根本就不存在,如果他找到了冯,他会发现冯是个战争罪犯,而如果他没找到冯,那么……(写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能不能找到冯·布劳恩)。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他找了这样一个朋友,在战火之中。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动人,他们一起谈论月亮、火箭,神父带他见到了真正的火箭。
澎湃新闻:你的小说中有很多硬汉,除了外公,《犹太警察工会》中的兰兹曼也是一例。他们性格的哪一方面吸引了你?
夏邦:或许部分原因是他们和我截然不同。我不是一个硬汉,我多话善谈,喜欢表达我的感情,我没有暴力倾向……我认为我从内心深处对沉默寡言的人感兴趣,他们相信行动大于言谈。从表面上来看,我和外公几乎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都截然相反。但是,我觉得我要是和人物没有共鸣的话,我是写不出他们的。
这种沉默寡言的性格也是上一辈人的特质之一,我们这一代更喜欢谈论事情、分享感受,我接受这一主流观点,但这是我后天习得的。我的家人都喜欢保密,让某件事过去的方式就是不去谈论它,我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我的性格里接受了这一方式,尽管我在理性上知道它是错误的。我理解不去谈论、对表达感受不耐烦的这种冲动,就外公而言,我还理解他的孤独、孤立,对他来说与自己相处、坚持己见能带来一种慰藉,让他能更好地渡过难关。在这一次层面上,我和他或许又没有那么大的不同。
澎湃新闻:外公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吗?
夏邦:是的,他的确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这是他一生中随着时间慢慢形成的。他在二战中的经历和他战后与外婆结婚、见证她生活在二战带来的苦痛中,还有他遇见冯·布劳恩,奉命去捕获冯,计划将冯绳之以法,最后却眼看着冯在战后平步青云,直接从支持他的社会体系获利,这一切都造就了外公虚无主义的价值观,让他越来越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尽管如此,他与此斗争,他不想完全放弃,他寻求意义,哪怕不是追寻“一切”真相,他也要追寻“一个”真相,比如挑战者号事件,他渴望解释一件似乎无端发生的事。人的一生或许没有什么目的,但至少可以有一个理由。
澎湃新闻:他对外婆的爱,他渴望修复她的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他自己的人生注入了一些意义。
夏邦:是的,爱是他抵抗虚无的诸多方式之一。
新闻推荐
来源丨一起拍电影作者丨魏建梅这一次,我们的确又被打脸了。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当下国内很多家长的“共识”。《起跑线》直面的就是有关孩子“起跑线”教育的这一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