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都到上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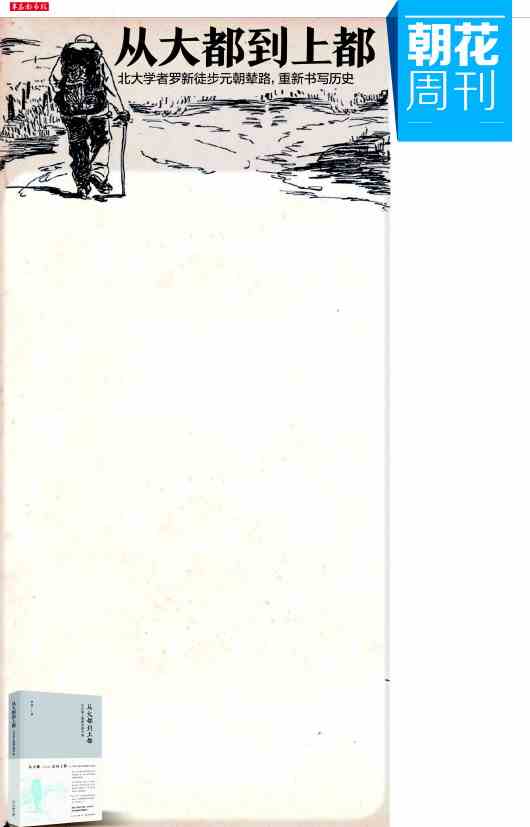
半岛全媒体记者刘依佳
“侍从常向北方游,龙虎台前正麦秋。信是上京无暑气,行装五月载貂裘。”
十五年前的春天,当北大历史学家罗新读到了朱有燉的这首诗后,开始对一条尘封了八百年的古道——从大都到上都——产生了兴趣。虽然罗新的研究领域是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并非蒙元明史,但这条元朝皇帝年年要走的辇路,仍深深地烙印在他心里:“为什么不自己走一趟呢?”
一年之前,罗新在网上发了一篇万字的行走“宣言”。时年53岁的他,终于要做这件惦记15年的事了。随后,他自古时大都——北京健德门出发,沿着古代辇路北行,历时15天,一步一步用脚丈量了450公里的河山,抵达上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
十五年的朝思暮想,十五天的徒步之旅,数十载的史学积淀,在这条曾经璨若星河又被历史尘埃深深掩埋的古道上,交汇激荡。回京后,罗新根据旅行笔记,又花了一年的时间,把历史的深思、人生的况味、对故人的怀念、对当下的思考,写成新书《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简称《从大都到上都》)。本期“快读”,就让我们跟随罗新,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的专家,从大都走向上都,于山川古迹的描述中,体会背后的历史、文化和由此生发的人文关怀和情怀。
辇路,是条什么路?
从大都到上都,曾是元朝皇帝如候鸟一般春去秋来的路,史书上称之为“辇路”。
那么,什么是“辇路”?
“忽必烈称汗后,建立了两都制,以燕京(今北京)为大都,以开平为上都,其中上都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政府以东20公里处。连接两都的交通道路共有四条,其中两条是驿路,但皇帝不走驿路,而要走专属性道路,即专为皇帝南北巡幸所开的道路,故称辇路。”罗新介绍,辇路共有两条,往返各走一条,由大都至上都走东道,由上都至大都走西道,这也是《扈从集》里提到的“东出西还”。半岛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古时元朝皇帝走一趟大概得20多天,比如史载1352年6月,顺帝从大都至上都用了24天,8月31日返回时走了22天。因为路途遥远,辇路中设有十八处供皇帝及扈从之臣休息的地方,称“捺钵”,“这是契丹语,汉语的意思是‘行在\’,只有辇路上才有捺钵。”罗新说,每个皇帝的行程都不是固定的,但多数来说,确实在几个重要的地方休息时间较长,比如古代叫“沙岭”的沟门,“还有比较靠近上都的几个大湖。湖边休息的时间长,主要是打猎,打天上的猎物”。此外,元帝刚离京时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例如走到今天长城附近的时候,就要休息个两三天,罗新说,主要是为了处理一些来自大都的事务。
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载入史册的古道多如繁星。这段元朝辇路到底有何魅力,能让一位史学专家在华发之年毅然放下一切,徒步全程?
“由于辇路禁人行走,非扈从皇驾者不能亲行其地。而扈从者中长于文翰且留有记录的人更少。所以造成了对辇路的认识有颇多争议,至今仍有模糊不清之处。”罗新说,十五年前,他也是在与同行的讨论中发现这一问题,从而萌生了亲自走一走的想法。罗新说,此外,这条路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及文化价值恰好与自己的研究兴趣相关。
“长城一带是我研究北方历史问题的一个窗口,元朝辇路中大有将近300公里的长城地带,我主要也是在这个路段里走。”罗新说,当年,辇路两侧水草丰美、山川秀丽,沿途城堡墩台林立,过往商旅不绝,煞是热闹:“这里是山川的终点,草原的起点,是自古以来从蒙古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特别是在明朝,两个政治体在此分割,农牧两种经济类型在此转变。因此,这条路是沟通长城内外、连接草原文明与农耕文化的历史走廊,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当罗新一再地问自己,他决定出去走一走,试着寻找自己所研究的那个遥远迷蒙的古代中国,与身处的当代究竟有何关联。于是,一个初夏的清晨,罗新来到北京健德门,请一位路人帮忙拍了张自己背对健德门立交桥的逆光照片后,就朝着遥远的上都明德门出发了——“古人出门都是起大早的,所谓披星戴月,乃是走远路的常态。前往上都的人,若要早早出发,就得提前一天出健德门,住在城外,以免浪费等候城门开启”——《从大都到上都》的开篇,也由此开始。
在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考察的方式多种多样,为什么非要选择徒步这种最艰苦、最费时的方式呢?对此,罗新回应:“后工业时代,当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得几乎不值得测量时,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在罗新看来,走路时进入的那种沉思状态,那分分秒秒和无意识的一步一步,能带给他极大的愉悦、头脑的清醒和心情的平静,“走在深山荒草间,人的视觉、触觉、味觉、听觉与大自然真真切切地发生联系,让我们更深地走向自己的内在。”罗新说,行走的意义,也许就在于行走本身。
书中的山川“带字幕”
1963年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这是罗新的公开履历。但在这众所周知的身份背后,罗新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许多面:比如,在进入历史研究领域以前,他就读北大中文系,热爱诗词和文学,有着固执的人文情怀,年轻时也爱听朱哲琴;比如,他的翻译水平很高,《从大都到上都》里所引用的关于国外旅行家的段落,几乎都出自他本人的优美译笔;再比如,他是徒步狂人,自言“性喜旅游,爱好广泛”……
作者的丰富,成就了作品的丰富与多样。
所以,读《从大都到上都》,记者始终无法把这本书归入某个清晰的类别,类似严肃的历史性学术著作或是纯粹的历史游记等等,更多的则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阅读感受:你若是历史系的专家或爱好者,书里自有精准、新鲜的专业养分供给与你:大到辇路沿途风貌及历史变迁、元帝出京时起居事宜、十八处捺钵及沿途各处古迹的前世今生、元明期间边疆各民族的融合史实等等,小到制酒技术是如何越过长城向外传播、明朝士大夫流行穿着的“马尾裙”的款式、长城以北的制备曾经优于长城以南等,字里行间,举目皆是。
如果你偏爱诗词歌赋,那也没问题。在书中,罗新开启了是“边行走边吟咏”的模式,但凡与元朝代辇路有关的古代诗词,都被他不留痕迹地镶嵌于路上的每一步,书中的每一页,甚至每一章节的小标题:在健德门,有元代诗人杨允孚的“今朝健德门前马,千里滦京第一程”;抵八达岭,王恽的《中堂事记》言犹在耳:“度八达岭,于山雨间俯望燕城,殆井底然”;至龙虎台,熊梦祥的《析津志》脑海升腾:“高眺都城宫苑,若在眉睫”……古文诗词,随处安插,却又不露痕迹,不显晦涩,足见作者功力深厚。
不露痕迹的还有属于现代人的优美金句:“挣扎多年以后,我们明白了,不是我们成就了旅行,而是旅行成就了我们。”“旅行就好比婚姻,如果你以为你能加以控制,那必定大错特错”……
无法控制的还有作者本人的回忆和对现实的思索:年少时不为人知的暗恋,三十年前半途而废的远足,风华正茂的女学生突然离世,浅淡之交的故人神秘失踪,“城中村”小月河的嘈杂与消亡,以及从第一辆都灵产的Itala汽车跑上了古桥广济,到如今桥身已成停车场的心痛……过去几十年来的人生悲喜、耳闻目睹,都因作者行经某一地点目睹某一场景,被恍然忆起,而后以不加掩饰、不作修饰之态,零星地散落在这条徒步之旅上……罗新坦言,这本书,也是他对一种纪行新文体的尝试,即“尝试把旅行写作与历史思考结合起来,让时间浸润于空间”。
也因此,在诸多名人对《从大都到上都》的评点里,半岛记者觉得最贴切的是学者蒙曼的读后感:“跟着罗老师旅行,山川都是带字幕的。”这位在央视诸多“清流”综艺节目里表现不俗的著名历史学者曾经师从罗新,她说,所谓的“带字幕”,是在阅读中不仅仅能看到旅途中的自然山川,还能看到山川背后的历史、文化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人文关怀,“这本书最大的好处,就是行万里路的背后是读万卷书的积累和思考”。
新闻推荐
吴君如:改名图个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