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典林 X 周逵 X 董晨宇:关于深度访谈 课堂中可能没讲过的故事
原创 新传研读社 新传研读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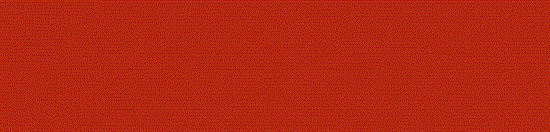 写在前面
写在前面
2020年4月14日的下午,在黄典林老师的质性研究方法网络课堂上,出现了两位年纪较大的旁听生。他们决定即兴“上麦”,一起和学生聊聊田野研究中的访谈经历(尤其是课堂和教材中可能不会讲的故事)。
聊天持续了两个小时,新传研读社的小编选择全程“悄摸摸”录音,并“快嗖嗖”整理出了这份极简版推送。希望三位青年学者的对话,能为你理解访谈方法带来“一丢丢”启发。
正文共8680字,可能需要16分钟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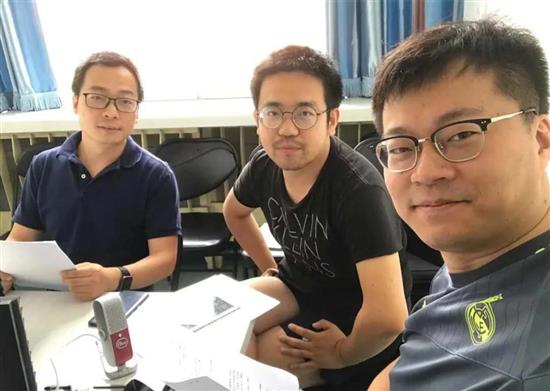 (假装合影:黄典林老师、董晨宇老师、周逵老师)
(假装合影:黄典林老师、董晨宇老师、周逵老师)
01.
教材能“教”我们做访谈吗?
 黄典林(以下简称黄):我先抛一个题目,听听两位老师的看法。你们觉得访谈的研究方法是可教的吗?
黄典林(以下简称黄):我先抛一个题目,听听两位老师的看法。你们觉得访谈的研究方法是可教的吗?
周逵(以下简称周):我觉得当然是可教的。当然有一部分是所谓的默会知识,是在经验层面的,但是我觉得,默会知识也有被转化的。可能最好的方法是带着一定的认知先去做一次到两次的质性研究,再回来看这些技巧性的东西,可能你的感受会深一些。还有一个最大的挑战在于,现在的质性方法教材,基本都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在中国搞质化研究有很多本土的特殊性,很难从这些教材中获得,所以还真的是需要你自己通过实际的去体会。
董晨宇(以下简称董):教材能给我们的是一个基础的工具包,就像是给了我们锤子,让我们用它来组装家具,但是这个东西本身是不能保证我们可以把家具装起来的。教材里经常会提到一些很有用的原则,比如提问者要简洁。刚刚做访谈的人,经常忍不住想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包括我们听讲座时,也经常会发现很多提问的人,站起来说了5分钟,一个问号都没有。这是教科书可以教给我们的技巧。不过,有一些问题可能就没有标准答案了,比如要不要对受访者分享自己的感受?其实难以给出一个确定的标准。
黄:我也跟学生讲了类似的观点。课上讲的这些原则都是学者基于经验梳理出来的,可能具有通约性,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你要区分不同的情境,根据特定的情境去调整,说白了还是一个经验的问题。
02.
在中国做访谈,有何特殊之处?
 周:我举一个具体的场景,我经常接触的调研有两种,一种是去各个地方电视台、县级融媒体;另一种是去一些商业网站、视频网站或者节目制作公司。这两种调研都是质性研究,但方法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如果你去偏体制内的地方,很可能就被带到它的场域里去。他们认为,有学者来调研了,我们要高度重视,首先肯定要安排好你们的住宿。这对你来说就是一个选择,你需不需要他们提供住宿?如果你跟他们走得过近,可能你就缺少中立或独立的观察角度;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跟他们把关系处好,可能你连继续调研的机会都没有。我们经常看到有一大堆人去调研,调研的形式就是去一个办公室,中间放着PPT,大家坐一圈,那边的人就开始讲,讲完以后这边提问,那边再回答,最后一起吃个饭,调研就结束了。但是,你认为这算调研吗?我认为这不叫调研,这就是一个PPT展示。很多学者往往就止步于此了,这样一来,你的研究很可能就是帮他们背书而已。
周:我举一个具体的场景,我经常接触的调研有两种,一种是去各个地方电视台、县级融媒体;另一种是去一些商业网站、视频网站或者节目制作公司。这两种调研都是质性研究,但方法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如果你去偏体制内的地方,很可能就被带到它的场域里去。他们认为,有学者来调研了,我们要高度重视,首先肯定要安排好你们的住宿。这对你来说就是一个选择,你需不需要他们提供住宿?如果你跟他们走得过近,可能你就缺少中立或独立的观察角度;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跟他们把关系处好,可能你连继续调研的机会都没有。我们经常看到有一大堆人去调研,调研的形式就是去一个办公室,中间放着PPT,大家坐一圈,那边的人就开始讲,讲完以后这边提问,那边再回答,最后一起吃个饭,调研就结束了。但是,你认为这算调研吗?我认为这不叫调研,这就是一个PPT展示。很多学者往往就止步于此了,这样一来,你的研究很可能就是帮他们背书而已。
黄:一些商业的媒体机构,也都有专业部门来对接调研。如果你直接和他们的PR对接,这种调研可能最后就让你被嵌入到它的公关机器之中。
周:是的,但这种调研在中国语境里往往是必须的。我觉得第一次调研可能是田野意义的pilot study,你不要指望任何有学术价值的发现,你大概摸清楚一下情况,大概知道王主任、赵经理、李台长是什么关系就行了。真正的调研是什么?等下一次,领导不在的时候,你可以和对方的年轻人直接聊天的时候,往往才是第一次真正的调研。但是很可惜,是大量的质性研究都是做了一次就没有第二次了。
这一点对于应用型研究也适用。我在2007年给一份报纸做企业战略的研究,我们的策略其实就是找一些比较非正式的场合,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轮流聊,不要那种群聊,群聊基本上没什么用。你要真弄一会议室坐下来聊,可能他就会有提防。我自己也发现,很多时候,前期其实铺垫的很好了,最后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跟他说,我们做个访谈,然而,对方一旦进入到正式访谈的节奏中,他说话就和平常完全不一样了。
黄:我们在课上讲的质化方法,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东西,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场景化的东西,你作为一个研究者,也要被嵌入到这个场景当中。董老师在做的研究主要涉及年轻人,比如他和学生在一起研究线上分手这件事;周老师会更多聚焦媒体从业人员。这两群人的差异性很大,也就对研究者提出了非常不同的要求。
03.
质化研究的资源与进入
 董:周老师刚才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进行第二次访谈,但研究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不是所有时候我们都有第二次机会。有时候我会觉得,你能做出什么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你掌握什么资源。
董:周老师刚才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进行第二次访谈,但研究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不是所有时候我们都有第二次机会。有时候我会觉得,你能做出什么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你掌握什么资源。
我们还要考虑一个问题,被访者为什么愿意接受访谈?我可以讲一个特别奇妙的经历。有一次我做访谈,被访者和我约到了一个地方,我到了那里才发现,他把我拉到了一个谈生意的饭局上,然后介绍我是某某大学的教授。当然这是极端的情况。更多时候,被访者可能是因为有表达欲望、寻求认同,或者仅仅是觉得访谈这个事儿有意思,想尝试一下。这种复杂性就决定了,不可能有一本教材可以被完全镶嵌到你的田野当中。田野是一个艺术,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像量化一样精确的操作指南,因此犯错误是经常的事情。它是一个充满了缺憾的东西。
周:刚才其实董老师说到两点,我来回应一下。第一是研究资源问题,我觉得很多学者都忘了,研究是需要资源的。很多人认为,我想研究什么就能研究什么。不是的这样的。很多时候一个研究问题我放在那要攒很久,我等到我有了充分的研究资源,不管是数据,还是人脉,还是说资金,或者是时间等等,甚至文献学术也是一种资源。这些比较充分了之后,我才可以去动手。就像我想做一道满汉全席,我现在只有豆腐丝,我怎么做?我们经常会碰到非常年轻的研究者,高屋建瓴,看得很远,我觉得非常好。但是这个时候,我其实不建议做那种太大的话题,因为可调度的资源太少了。
一些年轻学者现在想去做量化,我觉得并不是他真的对量化研究有充分的科学认识,而是收集数据方便,我弄一个问卷,在朋友圈转发一下,就可以写论文了,但实际上没有太大意义。什么是有用的呢?比如说我要研究一个游戏玩家迷群,问卷发给了第一个人,他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帮我转到一个玩游戏的大群,用一种滚雪球的方式,这个是有意义的。你把问卷发到朋友圈里,大家醒醒好帮个忙,这个就比较扯了。
第二,你进入田野的时候,要有一个身份,一个相对的姿势。我进去跟人家聊天,对方首先判断你是来干嘛的。你说我是个学者,大多数人对于质化访谈这种东西,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要借用一些其他身份,既可以在场域中以第三者的身份来观察,同时还不突兀。所以我自己去做田野,是以顾问的方式进去,因为学者有这样一个便利,我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了非常深入的东西。我觉得年轻学者还可以用实习生的身份进入。他可能只是帮着端茶倒水,坐在后面一排,所有人都能看到他,但却对他没有警惕。我原来在 MIT的导师叫Jing Wang老师,每年放暑假的时候,他都来北京的奥美当实习生,他后来写了本书叫Brand New China,研究中国品牌。但是中国学者可能就会觉得,你都混到教授了,还去当实习生?
04.
田野调查中,
我该何时披露自己的身份?
 董:这其实还引申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田野时,应该在什么时候去告诉他们,我是研究者。
董:这其实还引申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做田野时,应该在什么时候去告诉他们,我是研究者。
黄: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从伦理的角度来说,教科书里也都会提醒我们。前几年有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研究《中县干部》,作者在做挂职的时候,利用职务之便,对当地的官场的人脉做了非常详尽的研究,论文也写得非常好。但是论文出来以后,大家一个争议的焦点,在于作者并没有清晰告知这些调查对象,我是在做研究。对方把你当做一个朋友,在酒席里头,可能跟你闲聊中透露了很多东西,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伦理问题,我觉得对学术研究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悖论。我们如果如实相告,可能对我们获得某些资料会构成很大的障碍。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告知的话,又可能会涉及到一个伦理风险,我们实际上在利用对方。这个问题怎么平衡,中国学术界好像也没有一个标准的说法。西方大部分学者可能会赞同,你宁可研究打一些折扣,还是要如实相告。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我想肯定是要提前告知的。就是说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就录音,然后事后问对方,这录音能不能用,我觉得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彻底摧毁你们之间的信任。进一步讲,我认为这种没有录音的聊天,其实非常有用的,它应该占据你整个研究的很大一部分。我们不要认为开始访谈才算开始研究。从我从个人经验来讲,很多研究你到了正式访谈那一步时,其实已经定下了基本的方向,你提前应该已经了如指掌了。基本上我要访问一个人,大致70%的内容都在我脑子里头,这些东西是肯定会出来的,但是这话不能我说,必须他说。还有另外30%可能是惊喜,它既可以作为你原来研究假设的一个增量,甚至它能重构你原来的研究假设。但是我觉得,那70%是不可少的。所以我的处理方式,是大量聊天不用记录,你脑子里有了,对这件事增加理解了,就可以了。然后到某一个阶段,我要开始规范性操作了,我会选取几个被访者,做一些正式的访谈。
董:关于告知问题,我自己的策略是这样的。我正在做一个关于抖音直播的网络民族志,我肯定不能一进人家的直播间,就自报家门,问对方我能不能把你的直播间当成田野。这样的话,主播可能会觉得我脑子有问题。我会先挑选一些主播,去看他们的直播,然后我会从中再选几个进一步观察的对象,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基本认识了,然后我会私信主播,表明我自己的身份,说我想做一个关于直播的研究,能否继续在你这边做观察,并且一起聊聊。这个时候一般人都会答应。
黄:这种策略有一定道理。一开始,实际上你并不严格限定自己是一位研究者,就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观众。你是在做一个前期的抽样框。然后你在确定真正的研究对象时,你已经跟他们产生了某些互动,已经建立了一种初步的印象。这样既确保了你后续研究的有效性,同时又符合伦理的要求。
05.
我该怎样提问题?
 黄:刚才我们聊了进入田野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拿到门票。在很多田野中,访谈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如果我们去访谈一个著名人物,你的提纲可能已经比较明确了。但是在田野调查中,很多时候我们对研究对象是一无所知的,他就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那么,这个时候如何确定访谈的形式,它的是要正式一点,还是更随机一点,更close-ended一点,还是更open-ended一点?怎么平衡这个东西?你们自己的访谈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黄:刚才我们聊了进入田野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拿到门票。在很多田野中,访谈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如果我们去访谈一个著名人物,你的提纲可能已经比较明确了。但是在田野调查中,很多时候我们对研究对象是一无所知的,他就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那么,这个时候如何确定访谈的形式,它的是要正式一点,还是更随机一点,更close-ended一点,还是更open-ended一点?怎么平衡这个东西?你们自己的访谈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周:我觉得这取决于你和采访对象之间的权力关系。如果你和被访者在智力、理解力、表达力是相对平等的环境之下,可能正式访谈会造成负面影响会小、正面效应会多一些。但是,如果你和被访对象明显处于一个话语权力差距悬殊,比如说你要去访问一个大老板,他是一个明显要长于你、情商比你高很多的人,你坐下来跟他聊,很可能分分钟就被他洗脑了。就像某媒体这两天惹出很大麻烦的稿子,我认为记者完全就被说服了。她在单方信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之下,完全接受了那套说辞。有的时候,这种取得一些成就的人,通常是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他非常是果决的,因为他底下领导几千个人甚至上万人。你只是一个大学老师,哪怕是个大学教授,你平常也领导不了几个人。你的学生一共86个,可能有74个人不理你,还有2个把你拉黑。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是完全没有办法抵挡他的个人魅力,所以到那以后,你最后就变成一个不断表示赞同的人,加上对方可以帮你安排了食宿、机票等费用,你是出于一个完全的弱势状态。反过来讲,他接受你的访谈,其实是想拿你给自己做点政绩、文宣。所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你跟他约到总裁办公室坐下来聊,可能必须要经过这一步,但是你可能很难通过这样的访谈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对于这种质性数据要保持一个充分的警惕,就是不要太相信他。因为他的那套话术已经非常成熟了,你是第一次问他,可是他这个答案已经说给无数人听过了,他自己活在一个非常娴熟的话语当中,你是搞不过他的。
董: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的。如果我的研究方法只是访谈,比如说我访谈了30个留学生。这时候我可能会选择在刚刚开始时,用非常结构性的、封闭式的访谈方法,然后在访谈了两三个人之后,我可能会觉得,自己的一些问题是非常愚蠢的,根本没问到点子上。我要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修改自己的访谈提纲。比如说第一个被访者提出的一个观点,让我觉得很有启发,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开放性问题,去问第二个人。也就是说,我的访谈提纲是在不断修改的。
如果我做的事情更加田野,比如说,就在一个主播的直播间里面,呆上半年,跟这里面的十几个人都混的很熟,这个时候,其实我的访谈是非常去结构化的,甚至是即兴的。例如,突然其中有一个看直播的人给我发私信,他说你看直播间的某某人,是不是托儿?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了,我会通过日常交流去学习很多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所谓的常人知识。我们不要看不起这些常人知识,换句话来讲,质化研究者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摆低姿态。我们读完博士就一定知道的更多吗?不一定的,在你的研究对象所常年混迹的领域里,你其实就是一个小白。这个时候,所谓的访谈可能就是日常闲聊中展开的,比如在直播间里聊天、在私信里聊天,还有很多人和我加了微信,我们在微信里一起吐槽。他们全部都知道我的身份,我在哪里教书,他们还会给我的朋友圈点赞,甚至还有人专门来问我:传播学是什么东西?
周:我再补充一点,很多在田野当中的访谈,其实是以谈为主的,不一定要以访为主。访谈一定是以一个提问开头吗?我觉得在现实操作当中,大多数高质量的访谈不是以提问的方法开场的。如果你在一个田野里扎得够深了,你突然去问对方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会很奇怪,尤其在具体的情境当中,提问题有的时候并不是最优选择。所以很多时候,你想激发出对方的倾诉欲,或者激发出对方向你解释这个事情的欲望,你用陈述句甚至感叹句,会比提问更好,更能引发他的共鸣。
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去研究B站的up主,我们想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们可以直接提问:你们是想要得到经济上的回报吗?这是一种提问的方法,我觉得一开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熟了以后,我觉得你不妨变成一个陈述句或者感叹句,你可以说:“参加这种活动谁指着挣钱啊!”他可能就会说,那可不是,谁指着这点钱,老子家里4辆宝马5辆宾利,我还差这点钱?或者老娘根本不在乎这个,老娘就是图个开心。我的意思是,不一定要用问题的方法来获得答案,这是第一点。
06.
访谈时间到底要多长?
 董:还有一个质化研究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千万不要让你的被访者感觉到“被剥削”,这是我感触非常之深的,如果你发现他给出的答案越来越短,还比如他开始走神了,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结束访谈,感谢他,问他能不能之后再找个时间聊聊。如果你把对方问烦了,还继续咄咄逼人想攫取人家最后一点”价值“的话,那么第一,这样做是不符合研究伦理的;第二,往往你什么都得不到。
董:还有一个质化研究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千万不要让你的被访者感觉到“被剥削”,这是我感触非常之深的,如果你发现他给出的答案越来越短,还比如他开始走神了,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结束访谈,感谢他,问他能不能之后再找个时间聊聊。如果你把对方问烦了,还继续咄咄逼人想攫取人家最后一点”价值“的话,那么第一,这样做是不符合研究伦理的;第二,往往你什么都得不到。
周:我提供一个反面意见。在采访的时候,有一种方法恰恰相反,就是马拉松式采访。我见过很多老记者都是这么搞的,他们的采访时长是令人发指的,经常采一个人采七八个小时。我之前在凤凰的时候,采访的最长记录,就是我在做抚顺战犯管理所讲溥仪的一个纪录片,我采访那个人大概三天,每天大概6-7个小时。如果对方配合度非常高,我其实是可以“剥削”他的,因为很多东西聊的时间越长,对方的戒备心会越低,然后他会慢慢的由于各种原因,卸下一开始高度警惕时使用的那些话术。而且,针对一个问题,你可以反复问,要在他的每次回答之间,去比较差别。
你说的我是同意的,大多数人没有这么高的配合度你,一旦发现对方眼睛已经走神了,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有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尝试把他的兴趣点重新抓回来,这点挺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让对方是高度的进入到你的谈话里面去,让他不停地被挑战。当然,如果这些都不具备的话,我觉得分若干次访谈也是很好的。有些新闻采访也是这样,比如说我约到一个大佬,他说我一共就给你20分钟时间,我怎么办?我只能跟黄教授说,能不能这样,我们把20分钟分成三次,每次访10分钟,这样的话可能会把时间拉长,或者在第二次的时候,他对你有所了解了,可能实际上并没有这么苛刻,这种1+1+1大于3的情况也发生过。
黄:我作为第三个人的视角,我来谈谈我的看法。我觉得你们两个说的情况其实我觉得并不矛盾,因为你们实际上处理的是不同性质的访谈。像董老师讲的情况,他的研究目的非常明确,比如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想去做某个网站使用的质性研究,我觉得这种研究本身它的深度其实是相对有限的,所以对于每个单独的访谈对象来讲,我们访谈的深度、宽度,以及整个访谈的时间幅度,可能并不需要特别长。这种情况下,访谈就可以控制在一个比较半结构化的方式中去完成,它不是完全开放的,也不是闲聊的,也不是像问卷那种非常高度结构化的。我觉得大多数研究实际上做的都是这种意义上的访谈。周老师说的这种情况,实际上更多是你去做一个节目,关注某一个历史事件,或者某一个人的个人经历,这种访谈要求的时长是很高的,你只做一个半小时肯定是不够的,因为你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呈现出如此丰富和有深度的信息出来,所以它必然是一个长时段的事情。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民族志研究当中的访谈。它往往是非正式的,往往是以闲聊的方式出现的,所以显然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它可长可短,一定是根据访谈发生时所处的特定的情境来决定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一个乡村小学进行调研,老师下课了,我完全可以约他,进行可能会持续1-2个小时的访谈,我觉得完全是有可能的,也有另一种可能,我们见缝插针地利用她的闲余时间来进行一种非正式的聊天,所以我觉得这两种形式是互补的。
07.
研究结束后,我们还要与被访者保持人际关系吗?
 董:我想请教二位老师一个问题,在研究结束之后,你们如何处理和被访者的关系?因为在一些时候,被访者可能会有更多的期待,是我们无法帮他们实现的。
董:我想请教二位老师一个问题,在研究结束之后,你们如何处理和被访者的关系?因为在一些时候,被访者可能会有更多的期待,是我们无法帮他们实现的。
周: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明显觉得对方对你有更多期望的状态,他觉得你是大学教授,你可以帮他,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想象,所以一定要保持合适的social distance。就像采访的时候,我们通常不太愿意在人物类报道中,去采访那些主动要求被你采访的人,因为他自己动机会非常强烈。所以你可能自己稍微要清楚一点,我碰到过很多这样的学者、记者,他通常会跟这些被访者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中间距离。比如,你回微信的时候,首先不要让他觉得你是可以及时反馈他的,你慢慢就让他形成一个习惯,可能要等一两天才回我,这是一个常态。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做一些设计的。
董:其实我这个问题来自于之前出了一本书,叫《城中城》,作者因为学术丑闻好像已经离开学术界了。他在这本书中研究了芝加哥的一个黑社会团体。为什么他可以在那里面呆好几年进行田野呢?是因为黑社会老大一直误认为,作者要给他写一本个人传记,记录他戎马一生的黑社会生涯。作者这边就很暧昧,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就一直拖着。我觉得这可能是有问题的。
08.
除了写论文,我们还能做更多吗?
 董:我还想说一个我参与的研究。这个研究是我学生做的,我们在一起修改。访谈对象是中国的形婚群体,这是一群在主流文化看来非常边缘的人,他们非常需要理解。作为访谈者,我们的基本尊重如何表现?
董:我还想说一个我参与的研究。这个研究是我学生做的,我们在一起修改。访谈对象是中国的形婚群体,这是一群在主流文化看来非常边缘的人,他们非常需要理解。作为访谈者,我们的基本尊重如何表现?
我的感觉是,尊重并不是说我们一直强调说,我很理解你,而是我们真的花时间首先去了解他们了。所以我们刚才讲,访谈的准备工作特别重要。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周星驰跟柴静的一次访谈,柴静表达完一个观点之后,周星驰说:“你真的这么想的吗?”柴静说:“是,我是这么想的。”然后周星驰说了一句:“谢谢。”
除此之外,对于边缘群体的研究,我不太愿意把论文当成我唯一的目的。我希望可以在论文发表之后,也可以写一个不那么论文的东西,让更多人去理解他们。Daniel Miller曾经说,他自己的研究项目往往可以写两本书,一本是给专业学者看的,另一本是给老百姓看的。
黄: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在方法课里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如果你发个问卷让大家填,然后给他一个小礼物,实际上是一种交易关系、一种利益关系。刚才董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我是非常赞同他的,我们能不能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变成一种更多元的关系。我们最终发表的那个论文,其实可能很少有人会看到,因为论文实际上是写给专业研究者看的。那么,怎么通过特定的方式,把我们理解的一些东西反馈给研究对象呢?在研究方法中,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互惠原则。就是说我从你身上了解了很多对我有用的,我也希望从我的最后的产出中,能够对研究对象表达一种理解、一种支持、一种呼应,或者给他提供一个新的看待问题的视角。所有的研究者都应该考虑这一点。
周:我想补充一点。被访者有时不一定能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当中。当年李银河写的中国性少数群体,那时三十多年前了,当时很多同性恋者在家里关起门,躲在被窝里偷偷看,说有一个北京的学者研究了我们这个群体,我们叫同性恋,我们不是病,我们就是一种性少数群体。他们看的热泪盈眶,说原来我们是有一个共同体的,我们的社会身份应该被承认的。所以说,对于研究对象,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给他个纪念品,我们还可以帮助他更好的认识自己。从这一点来讲,无论是好的报道、还是好的研究,都是这样的。因为你帮助所有参与的人,包括你自己更好的认清楚你们的位置。
原标题:《黄典林 X 周逵 X 董晨宇:关于深度访谈,课堂中可能没讲过的故事》
阅读原文
新闻推荐
任鲁豫佟丽娅《战“疫”故事》节目历经风雨与岁月,神州大地会竖起一座座不朽的丰碑。它们有的是时代洪流中的中流砥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