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敏:进入“串”的万妙之门 灯过马走 衣袂飘然
原创 鲁敏 文学报
伴随第七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揭晓的,是我们邀请了八位获奖者从各自文学观念出发,一起来探讨当下文艺评论环境里,如何“朝向“真”的批评语境奋力前行”。
点击图片观看颁奖短片
这些获奖者或是评论家身份,或是作家身份,或是横跨两者兼具一身,他们无一例外都尊重且期待着文学批评展现应有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贴近文本内部联结写作者的心灵,并将其拖入到当代历史的核心问题中去评价。
今天的文章来自作家鲁敏,她从旧时曲艺梨园界封箱演出有趣的全体大反串,引申到文学界在“串”这件事上的驾轻就熟,诗人串小说家、小说家串编剧、虚构串非虚构、作家与评论家互串,而她也顺便解答了读者此刻最大的疑惑:如何“串”出新意妙趣?
串:万妙之门
文 / 鲁敏
 那种复杂又纯真,混沌的饱满多汁、活力肆意的高超之作,通常符合两点,一是写作者的原形,自有足够的体量与圆满,二是对所串之作,是出于无心机的赤诚行动。
那种复杂又纯真,混沌的饱满多汁、活力肆意的高超之作,通常符合两点,一是写作者的原形,自有足够的体量与圆满,二是对所串之作,是出于无心机的赤诚行动。
旧时曲艺梨园界有封箱演出的传统,众人江湖奔走,台前幕后一年,高高兴兴演上岁末的最后一台,然后把服饰戏箱封起,就此歇息,过年大吉哉。封箱演出或是全班合演,或是顶梁挑班的角儿每人一出拿手戏,或是全体大反串——大反串是最热闹有趣的,眼看着花脸大净扭扭捏捏扮起闺门旦,闺门旦鼻子上却贴起丑角的豆腐块,斯文巾生武起剑来串演刀马旦,持重老苍头翻作利嘴俏红娘。像南京的省昆小剧场,每到这样的反串大戏,票子是老早就一抢而空的,每一个角儿上台,从亮相到圆场,从念白到腾跃,下面都是一阵阵的喝彩,比起普通戏码来,更动人心。
 《贵妃醉酒》 关良/绘
《贵妃醉酒》 关良/绘
何为?因这样的观看里,起码有两三层的意思在。
一是演员原先都有专攻独擅的扮角与拿手绝技,老戏迷都是“看惯”和“熟知”了的,不管他如何改头换面,老行当的底子总在,他一亮相,老戏迷的喜悦就在于,哦,我一眼就看出来,是他,还是他,就是他呀。
二来因是封箱大吉,图的是同庆同乐,故反串行当往往差异较大,以求谐趣,可能小贴旦不那么灵动,大武生动作稍显单薄,杜丽娘的少女心会破绽出粗大相,但总归还是依着数百年的舞台程式走,观众也自会在这种意外的落差中,获得否定之肯定的观赏感。看哪,他现在成了 “她”,他不像“她”,可他也是“她”呢。
还有第三,如果是极出色的反串,演员原来的功夫好,他对新串的行当与角色,会有他的理解,尤其旦生互串、丑净互串,原来就是台上老搭档,故这种理解里,会有长期对手、而今调换位的体悟,给戏垫戏、念白配合,会有意想不到的融合,更会有些巧思与临场发挥,从而形成新的审美创造,哪怕明显打破程式之规,观众仍会为此心领神会、轰然叫绝,因台上台下都知道,这种创造力唯有借反串之机,方能阴差阳错而生。
梨园界只是岁末封箱时大家串角串行开心一番,文学界可是向来有此格局,大部分写作者,生涯之中,都会串上两三种文体。比如诗人串小说家,林白、海男、韩东。小说家、诗人与编剧的互串,刘恒、邹静之、严歌苓、王刚。非虚构与虚构的互串,如梁鸿、宁肯。包括涉足儿童文学的,张炜、叶广芩、周晓枫等。也有作家与评论家与学者的之间的“界别串”。小说家格非的《雪隐鹭鸶》,是他研究《金瓶梅》的菁华之书。小说家毕飞宇的《小说课》以独成一家的文本精读来解剖中外经典。评论家李敬泽那本杂糅考古学博物志或幻想书的《青鸟故事集》。作家韩少功作为译者的、带有他个人风格的《惶然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小说家邱华栋在《红楼梦》《金瓶梅》等明清版本学上的专著。小说家叶兆言从城市史角度著写《南京传》。而作为评论家与学者的李陀、吴亮等也各以长篇《无名指》《朝霞》而自如出入小说之域……这只是随意抓取的,实际上,这可以没完没了拉出很长的单子,因一个气象混沌的写作者研究者,不讲全把式,十八样长短兵器中,有一两样高举精进,有三五样耍玩于股掌,也是常情。或者说,在其漫长路径与自我养成中,各文体、各界别的滋养与习得,也是必经之途、应有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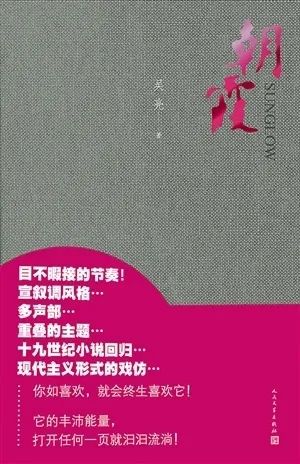 但在文体和界别上交叉跑动的写作,与一条道儿黑甜到底的写作,到底有些不同,还是值得说几句。
但在文体和界别上交叉跑动的写作,与一条道儿黑甜到底的写作,到底有些不同,还是值得说几句。
我们平常听得最多的,是说,是否有过诗歌写作的经验,对行文质地的锻造,殊为不同。此话自然有些道理,“串文跨界”的差异,常常会体现在文字,语感,节奏这些“肉眼可识、一望而知”的层面,就像戏台上的亮相,是步法与台风。有阅读经验的读者,会像戏迷一眼认出老相识,看,就是他这个味道。写作者初始方向的审美训练与肌肉记忆,会像版权所有的水纹印,翻到哪一页都会浮现在读者眼前。尤其是诗歌,它所打在文体页码上的水印,通常是加分的,其含混与歧义,凝练与节制,常会使叙述语言明显高出一个身位。
也有看不出任何水印的,原形彻底隐身,完全的改头换面。比如像马尔克斯,最近读到他一本非虚构,是他以66岁高龄专门采访写作的《一起连环绑架案的新闻》,我自也怀着特别的期待,但真的,这就是一本标准的老老实实的非虚构。这样说吧,同样是小说家写作非虚构,我认为卡波特比马尔克斯干得漂亮。卡波特带着小说家的独有体察,在《冷血》的全部事实之外,你总能看到一双考察诡谲人性的深切凝视,看到藉藉无名者在命运之手中,如何倦怠地彼此踩踏、先后湮灭。而马尔克斯所面对的素材,其繁杂程度更甚,在连环绑架案与哥伦比亚的毒枭与政府黑洞的精密编织中,你可以读到一切“大”的东西,权力、国家、罪恶、腐败、金钱、政客、媒体、黑帮、种族等等,但 “人”呢,被遮盖了。也可能马尔克斯不喜欢串味儿,他就是想写一个正宗的非虚构范本,他做到了,但作为读者,我感到挺失落的。他的扮相真不该是这么样一个超级记者,他应当演得“糟”一点,时不时露点他本来的魔幻小尾巴才好。我不知道,可能这样讲有点失敬,他真不如另写一部 “事先张扬的绑架案呢”。
 《一起连环绑架案的新闻》就是一本标准的老老实实的非虚构
《一起连环绑架案的新闻》就是一本标准的老老实实的非虚构
 满是水印、全无水印,或者都不是最佳效果,起码不能算是最有特色的贡献。我这大概也是有点儿出于效率的算法,是觉着,文体与界别的串行,不是从这个“1”,到那个“1”,写作者内在独有的“1”,与另作扮相的“1”,这两个“1”,因对审美维度的不同截取与侧重,会相互搅拌,撕扯又缝合,从而在形成一个并不等于 “2”的独有之好。毕竟,每种文体、每个界别都有着通往世界的窄门,当两道窄门在同一个写作者身上互通,应当会在创造上产生合力的迸发。
满是水印、全无水印,或者都不是最佳效果,起码不能算是最有特色的贡献。我这大概也是有点儿出于效率的算法,是觉着,文体与界别的串行,不是从这个“1”,到那个“1”,写作者内在独有的“1”,与另作扮相的“1”,这两个“1”,因对审美维度的不同截取与侧重,会相互搅拌,撕扯又缝合,从而在形成一个并不等于 “2”的独有之好。毕竟,每种文体、每个界别都有着通往世界的窄门,当两道窄门在同一个写作者身上互通,应当会在创造上产生合力的迸发。
可以先看看茨威格。他可谓是文体上的练家子,举凡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游记、文论、传记等等无一不涉。他的小说影响甚大,我上中专时一度十分迷恋,导致后来对强烈缠绵的抒情有点敬而远之。他因为写了《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与魔鬼搏斗》(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三作家传》(卡萨诺瓦、斯汤达、托尔斯泰)等,一时被戴上“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的帽子,这帽子合适吗,我保留意见。但此处可讲讲他另一本仍可归于传记类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原因就是,这本书算是体现出小说家与传记作家的“1+1”了。
此书语感很差,可能是翻译之故,也可能茨威格有意放弃了作为小说家的叙事水印,整体读来硬绑绑的,即便如此,仍然藏不住茨威格所特有的“强烈抒情性”,他会把人类文明的走向精缩到事件中的个人意志上,把历史推演而成的风云际会给集中到一个非常狭窄的薄片儿里来无限放大。这是很是小说家趣味的,以英雄史观来取代唯物史观,至今我们仍可在好莱坞电影中可以看到这一趣味的延续。就在这本《人类群星闪耀时》里,茨威格会把拜占庭帝国的陷落,精确归罪于他们对一个叫做凯尔卡的小门的疏于守护。而滑铁卢之败,罪不在拿破仑,而在他手下一位名叫格鲁希的将军,茨威格以惊人的篇幅和语气描写此人的愚蠢顽固,是他,在关键时刻的决策造成 “历史与人类命运”的引擎制动,从而使法国失掉了整个战争。而陀斯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成为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于他曾因政治活动被处死刑,而行将执行之际,一纸官文来到,改变了他的死亡轨迹,正是这一刻,是陀氏一生创作与思想的转折点,他成了一个伟大的作家,而不仅仅是一个作家,等等。作为小说家的茨威格显然非常癖好于考证并主张一个独特的 “历史瞬间”,他的历史不是渐变的趋势,总是激情的断崖或急转弯——正确吗,难说,有趣吗,有一点儿。起码茨威格为非虚构的历史书写提供了一种“他的”写作法。
 茨威格为非虚构的历史书写提供了一种“他的”写作法
茨威格为非虚构的历史书写提供了一种“他的”写作法
 相较茨威格,桑顿·怀尔德的“复合性”写作法就深沉多了。他以剧作家名世,与尤金·奥尼尔、阿瑟·米勒、田纳西·威廉斯并称四大剧作家。他的《我们的小镇》因为构造简洁,且极易本土化,成为全世界业余、学生、试验剧团等 “穷团”最爱重排的剧本,比如,台湾果陀剧场出品的《淡水小镇》版,即长演26年不衰。此剧不展开,讲怀尔德串角所写的小说《圣路易斯雷大桥》。
相较茨威格,桑顿·怀尔德的“复合性”写作法就深沉多了。他以剧作家名世,与尤金·奥尼尔、阿瑟·米勒、田纳西·威廉斯并称四大剧作家。他的《我们的小镇》因为构造简洁,且极易本土化,成为全世界业余、学生、试验剧团等 “穷团”最爱重排的剧本,比如,台湾果陀剧场出品的《淡水小镇》版,即长演26年不衰。此剧不展开,讲怀尔德串角所写的小说《圣路易斯雷大桥》。
仅薄薄120页,怀尔德却以此书入选美国图书馆二十世纪百本最杰出英文小说,并拿下1928年普利策小说奖,从而成为唯一同时获得普利策小说奖(一次)和戏剧奖(两次)的作家。我也极爱这部小说,独立看小说本身,其结构主题调性,皆是上乘,显现出杰出的才华,但读到最后,会发现一个深藏于文本背后的核,这个核也是怀尔德在他的戏剧中始终追问的:生而为人,你何时会死,你因何而死,你死而何为。他简直太勇敢了,也许只有戏剧家才有这样的胆气,以如此精短的文本去触碰人类生死之惑的根本性疑难,这把永远锋利的悬剑,瞄准着每一个复杂孤独的个体。当然,我不会用这本薄薄的书去与《百年孤独》之类的大部头相比,不是说比不过,这就好比拿云雀与鲸鱼相比——这对二者都是不公平的。但怀尔德偶尔这么一串角,却把戏剧+小说的“串”作之力给拉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标,对他本人而言是这样,对文学史也是这样。这就是我所说的,效率与综合意义上的贡献。

 桑顿·怀尔德的小说《圣路易斯雷大桥》把戏剧+小说的“串”作之力给拉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标
桑顿·怀尔德的小说《圣路易斯雷大桥》把戏剧+小说的“串”作之力给拉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标
还有两个最妙的“串”角大作家,简单提一下,因为他们实在是需要长篇大论。一是朱利安·巴恩斯,他的《福楼拜的鹦鹉》与《10 1/2章世界史》写法怪而高超,几乎带点戏谑地,把虚构与非虚构给 “串”在同一个新文体里,假托虚构的外部事件,而在内部串起历史的真实碎片,见史料功夫,也见小说家的大本事,可以说是蛮典型的因 “串”而起的文体贡献。二是格雷厄姆·格林,他一生获得21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最终获得的却是美国推理作家协会最高奖:大师奖。他较刻意地把自己的创作分为推理类和文学类,文学类的大家都熟悉,如《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权力与荣耀》《命运的内核》等,在宗教、政治与人性的探索上极为深远,而他的推理类间谍小说,就算他自己再想摘清,还是有股子“文学正典”的美妙气息,我向来深爱他的这一块创作,如《一支出卖的枪》《布莱顿硬糖》等,个人是觉得比专攻侦案的阿婆、雷蒙德·钱德勒等要余味深长得多,后两者的话,固然精巧、紧密、耐心,可怎么读都只见智力与匠机之心,就是总差点“文学”,而一旦没了这个,读完了,是真的太空虚了。

 朱利安·巴恩斯(左)和格雷厄姆·格林都是“串”角大作家
朱利安·巴恩斯(左)和格雷厄姆·格林都是“串”角大作家
如果再把这个“串”拉开一点,其实作家学者还有更大范围艺术门类的兼及,这向来也是文人传统,所谓琴棋书画是也,不谈古人,哪怕就是看看今人的朋友圈,亦可小见一斑,这里不作展开。艺术门类的串门子其实是互相的,艺术家串到写作上来的也颇有佳作。好几年前,画家朱新建出过一本随笔集 《打回原形》,写得轻松又高级,简直太好了,处处见三观,见他的落拓豪放,那阵子我老跟人推这本书。艺术家徐冰的一册《我的真文字》算是艺术来路与美学偏好的夫子自道,像我们这样的读者,当随笔来读读,也觉精彩之极。徐冰不仅是谈他文字观的流变与创造,还有许多生之际遇,人与艺术的背离与重逢,很有意味,绝对大于许多的美学随笔或艺术专论。对了,还有《魔灯》,我很想单独给写它一篇文章,这是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自传。各国导演的自传近些年出版很多,日本韩国欧洲各国的都有,可有些实在也是写得可怕,东一脚西一腿,散得不知所云。可伯格曼这本,真的具有很强的控制感与文学性,有价值观的突破与自洽,也有精心的伏笔与呼应,所涉多位人物,皆是活灵活现,害得我一边读一边把相关电影给补了一遍。


 艺术门类的串门子其实是互相的,艺术家串到写作上来的也颇有佳作
艺术门类的串门子其实是互相的,艺术家串到写作上来的也颇有佳作
——怎的就有这么大力道呢,我想就在于这种创作里的复杂又纯真,混沌的饱满多汁、活力肆意。这种高超之作,通常符合两点,一是写作者的原形,自有足够的体量与圆满,二是对所串之作,是出于无心机的赤诚行动。我们也常看到有大艺术家“专门坐下来”写随笔谈美学搞起写作来,他原来的架子端着,新扮的架子也搭着,这就难以浑然了。所以反串之作,要忘了原样,也要忘了新串,且这两种相忘是心理上的,在行动与过程中,两者却在真切的揉杂与勾连中,里应外合,成就一种异质的创造力。
唉呀,好像说得有点玄了,想起戏剧术语里讲舞台上的圆场,常说,圆场一转,转,为万妙之门,这里借用一下,串,或也为万妙之门。灯过马走,衣袂飘然,其妙正在有形无意之间。
当然,妙品其趣在妙,能不能成为臻品,也得两看。本文中举的大多是由妙品至臻品的例子,正因为他们“留下来”了,那些没有留下来、未被看见的尝试,恐怕也是宝贵的勇气与基石。其实所有的创作者,在漫长且默默然的自我耕作中,都是一边海纳百川、旁及涉众,一边在自己的专攻上苦心孤诣,这当中,有的另起串行,成其妙作臻品,也有的化于无形,以无用之用,归力于终极巅峰,各有各好,各拓其道——哈,这结尾,可真是没趣。
稿件责编:傅小平
新媒体编辑:李凌俊
配图:出版书影、资料图

文学照亮生活
网站:wxb.whb.cn
邮发代号:3-22
原标题:《鲁敏:进入“串”的万妙之门,灯过马走,衣袂飘然》
阅读原文
新闻推荐
“闹”是一个基本的字眼,太原人喜欢用“闹”来表达一切,“闹”的意思近乎于“干”“抓”一般。九朝古都太原,古称晋阳。这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