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奇岚:从文学到艺术 我们如何为记忆命名?
中信大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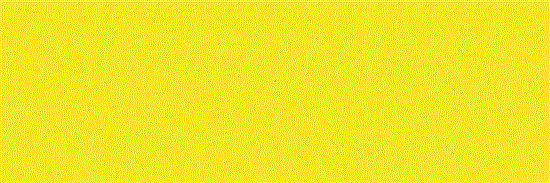 “大方live”是中信出版·大方的活动品牌,每月定期推出系列线上主题分享,收听来自文学艺术界的新声,激发不受时空限制的交流,建造无形却热烈的现场。
“大方live”是中信出版·大方的活动品牌,每月定期推出系列线上主题分享,收听来自文学艺术界的新声,激发不受时空限制的交流,建造无形却热烈的现场。
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回不去的地方和再也见不到的人,唯有记忆,能让它们永远鲜活。因为一场疫情,“失去”的体验在今年变得尤为深刻。在本月的大方live中,我们共读几本“记忆之书”,在字里行间,重回现场,与那些无法忘怀的和难以割舍的,再度相逢。
本期分享人是作家、策展人沈奇岚。作为德国作家沙朗斯基首部引进国内的作品《岛屿书》的策划人,她和我们聊了聊这位作家的新书《逝物录》。她认为,与召唤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岛屿书》相比,记录了12件逝去之物的《逝物录》是一本向内的书,召唤的是一种深层的情绪。如果说书写可以挽留记忆,艺术也是人类追寻逝去的重要方式。作为艺术策展人,沈奇岚还在本期中分享了里希特、基弗、波尔坦斯基等用独特方法雕刻记忆、处理创伤的当代艺术家及作品。 沈奇岚,作家,策展人,文化学者,经常与国际文化机构和美术馆合作各种论坛、学术研究和展览项目。曾任《艺术世界》杂志社编辑部主任,中南传媒浦睿文化艺术部主编,现兼任《书城》杂志编委。著有《我愿生命从容》《那个姐姐教我的事》等。
沈奇岚,作家,策展人,文化学者,经常与国际文化机构和美术馆合作各种论坛、学术研究和展览项目。曾任《艺术世界》杂志社编辑部主任,中南传媒浦睿文化艺术部主编,现兼任《书城》杂志编委。著有《我愿生命从容》《那个姐姐教我的事》等。
从《岛屿书》到《逝物录》
多年之前我在出版社工作,引进、出版了沙朗斯基的《岛屿书》。这本书关于世界上的各种神奇岛屿,故事写得非常冷静克制。这本书说,岛屿有如世界剧场,天堂是岛,地狱也是。那时候这本书已经拿了“世界最美的书”的殊荣,所以在做《岛屿书》的时候,下了很大的功夫,特别是在装帧上,《逝物录》肯定也是如此。 《逝物录》
《逝物录》
[德] 尤迪特·沙朗斯基 著 陈早 译
中信出版·大方 2020年4月
《岛屿书》和《逝物录》这两本书在质感上,一个是向外的,一个是向内的。《岛屿书》更加像是某种奇闻异事录,召唤的是好奇心和想象力,召唤的是知识的乐趣。《逝物录》是一本向内的书,召唤的是一种深层的情绪,不单单是对知识的满足。这本书当然也建立在知识考据上面,但还尝试了各种叙事可能,就像一部有很多镜头的电影。你会发现《岛屿书》像用无人机拍的岛屿故事,都是俯瞰的角度,用深沉的BBC一样的旁白讲故事,这是《岛屿书》的风格。但是《逝物录》的风格很多变,一会儿是打了柔光的,用了滤镜的,关于过去的一段时光的特别美好的回忆。一会儿是非常凌冽的,风格阴郁,长镜头,人物从头到尾都不怎么说话,会让读者觉得很压抑。一会儿又像是一个内心剧场,像一个人的喃喃自语,可以把它当作舞台剧去看。所以《逝物录》的质感很丰富,很有魅力。
作家有让逝去之物复活的能力
《逝物录》我最喜欢的有好几篇,其中有一篇《里海虎》,写得酣畅淋漓。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里海虎,而对于作者而言,她要去想象一个远古的生物,呈现生物的凶猛,是一个艰难的挑战。里海虎这种动物在古诗人的记录中雄风凛凛,它的野性让人恐惧,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是压轴大戏。在万人的嗜血呼喊下,它进行扑杀。这种描写其实是超级有挑战的,作者完成得非常好。书里面说,“他们让死刑和戏剧杂交。这些充满原始力量的动物被允许活,正是因为注定要丧命于痛苦的供人消遣的死。”所以看着《里海虎》的故事,我就一下子醒过来,精神大振,酣畅淋漓,字里行间有种血色在流淌,让我觉得吓了一跳。这还是写《岛屿书》的作者吗?她的笔触竟然这么凶猛,把我们带到了里海虎的生死场,这种时候让我觉得作家是有能力把一件已经不存在的事物在当代复活起来的。 葛丽泰·嘉宝
葛丽泰·嘉宝
另外一篇比较容易进入的是《蓝衣男孩》。《蓝衣男孩》讲的是作者想象中的葛丽泰·嘉宝,一个电影明星。作者很细腻地模拟了一个创造过辉煌的女明星的心理剧场。当默片的时代逝去,还住在豪华酒店里的女明星如何度过自己的下午?那是一个独白式的叙述,这种独白让人觉得作者好像非常了解女明星。看的时候,我很受启发,因为它会让我想起前不久刚刚拿了奥斯卡奖的电影《朱迪》,讲的是一个走在下坡路上的女明星的生活,一边破碎,一边发光,一边给予,但最后你会爱上她。尽管她刻薄、古怪、敏感、难以相处,但她创造过她的时代。里面有一句话很打动我,“I still believe in it. The love you find with your audience. A good night.”就是“我依然相信和观众之间的爱”,只有相信这一点的人才可能在舞台上真正给予、真正发光。而这种感觉在看沙朗斯基写的葛丽泰·嘉宝在午后的喋喋不休中也能够感受到。
我再分享一个我觉得不得不提的故事,是《萨福的爱之诗》。萨福在文学史当中是以写作迷人的诗歌著称的,但留下的只有传奇,没有诗歌。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所有风月场所里面都传唱着她的诗歌。但是中世纪之后,就没有人再知道她写过什么了。沙朗斯基对萨福做了很详尽的文献梳理。在前半部分它像一份娓娓道来的论文;重要的是后半部分,进入了一个很深刻的探讨,讲女性之间的爱何时可以被承认。Lesbiazein这个词,意思是“像莱斯波斯的女人那样做”,因为当时萨福所在的岛就是莱斯波斯岛,和萨福一样优雅,和想象的萨福一样情色。后来这个词却演化成了有伤风化或者违反自然的性行为。历史是不公平的。作者在叙述和探讨萨福当中,在历史演变当中,慢慢地把文章展开,而这时候你会觉得萨福其实不是单独的女诗人,她其实是一个象征,她是关于乌托邦式的爱。 《燃烧女子的肖像》剧照
《燃烧女子的肖像》剧照
去年挺红的一个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我觉得创作者一定也是把萨福和莱斯波斯岛作为心中的意向去创作的。这个电影就像一个发生在莱斯波斯岛上的故事,一个女画家受到委托,需要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一位小姐出嫁前的肖像。她们在孤岛相依为命,白天女画家悄悄观察这位小姐的一举一动,到了晚上开始下笔。她们互相吸引,互相凝视,互相倾慕。这两位主角就像萨福的诗歌中所写的,“你牵魂一笑/我就胸中心怯;/我凝眸一瞥,/就哑然失声”,美得不得了。在《燃烧女子的肖像》里面有一句台词深深打动我,“In solitude, I felt the liberty you spoke of. But I also felt absence.”“我能感受到你说的自由,但同时我也感受到你的缺席”,这是一种很深刻的爱。这就将萨福的爱之诗延续到了当代。
记忆是什么形状的?
《逝物录》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是关于记忆是什么形状,以及怎么给记忆一个容器。我们写日记、发朋友圈,这些是记忆吗?是记忆,但它是完整的记忆吗?要打个问号。
说到记忆的形状,我想起在《哈利·波特》这本书当中,有一个简单的回答,用魔法棒一挥,人就会有记忆出来,是液体状的,把它还原到记忆皿当中,大家就可以看到当时当刻的情景。也因为这个原因,哈利·波特可以看到斯内普为什么要保护他以及最终那个让所有人都感动的秘密。这是很美好的一个描述,但它就有些简单了。在我心中,关于记忆是更为复杂的。
好的文学作品,往往都是对记忆的雕刻。比如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种记忆绵绵不绝,写下午茶可以写几十页,但是进入这个“流”当中,有妙处。比如说奥尔罕·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里面会有很多物件,小狗摆设、烟灰缸、纸牌、钥匙,还有4000多个烟头。有一年我去伊斯坦布尔,慕名去看帕慕克做的纯真博物馆,在里面果然是感觉到了那种执迷,就是一个人对一段感情的无限执着,你就会相信这段感情可能真的发生过。纯真博物馆就是帕慕克的《逝物录》吧。
另外一个关于追忆的经典文学作品是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它也有很好的影视作品,但在文字中更能体会那种流逝和无法捕捉的、浪漫的、堕落的、无可挽回的心情。你没办法拒绝这种燃烧的心。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第一段你就知道她是在回忆,而且她是在回忆一段已经逝去的情感,但它永远跟自己在一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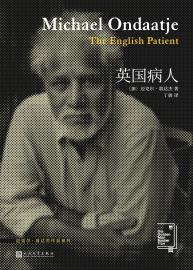 《英国病人》
《英国病人》
[加] 迈克尔·翁达杰 著 丁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8月
因为目前为止,我们都在努力地以人文主义的角度去思考记忆的好处,以及写作能够呼唤记忆的这种神秘魔力。现在科技如此发达,所以我想再补充一个作品。在特德·姜他的《呼吸》中有个短篇叫《双面真相》,他在里面重新探讨了记忆这个事情,它跟我们之前分享的所有这些作品不太一样,因为它会回到记忆最初的发生地,然后去思考如何去产生记忆。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反思,就是我们更容易去认识到读写能力的益处,却难以察觉它让我们付出的代价。《双面真相》里面是双线叙事,一个是讲在未来,每个人都能够调取自己的记忆,就像一段视频一样,然后去确认这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但有些人是拒绝这个功能的,因为它是一个科技公司提供的服务。另外一条线就是讲当时的欧洲殖民者到了一个原始部落,带去了文字记录,但也让大家意识到文字的局限性。在这小小的短篇当中,我觉得人们会再次去思考什么是记忆,什么是真相,什么是幸福。
当代艺术中的废墟叙事
在德国当代的艺术家里,有非常多以德国历史以及自己的记忆为主题创作的当代艺术家,跟大家分享几位。首先是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他的画作是至今为止在世的德国当代艺术家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也是最贵的。他的绘画方法影响了无数人。 格哈德·里希特
格哈德·里希特
里希特出生于1932年,他是在德累斯顿附近出生的。德累斯顿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已经成为一片废墟,被炸得几乎看不出原来是什么样子了。这是他的童年回忆。他在东德接受的是写实的训练,他对这种训练并不以为然。后来他就到了西德,去追寻自己的艺术生涯。寻找自己的艺术道路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必须要回到自己的童年创伤里面去,去直面二战纳粹的历史。他画过几幅非常沉痛的关于家族历史的作品,比如说他的《姨妈玛利安》。他的画有点像老照片的自然褪色,就像是亲戚们在他的回忆中的流动。他的姨妈是真实存在过的,但她可能有精神疾病。那个时候纳粹政府推行优良人种计划,患有精神疾病的姨妈玛利安被拖到了特殊的机构,成了被清理的对象。她的死与政治相关,但里希特并没有直接表现政治,而是以接近真实的方式把记忆中的姨妈玛利安呈现给观众。 里希特作品《叔叔卢迪》
里希特作品《叔叔卢迪》
另外还有一个作品是他的《叔叔卢迪》,画面冷静客观,近乎是纪实摄影。卢迪看上去像是一个比较和善的的亲戚,但他穿的是当时的军装,那是一段让人不堪回首的但必须直面的历史。里希特把自己的情绪克制在了画布之外,他画的画像是梦境中的回忆,又像是抽屉中的一张老照片。他说,“摄影要比美术史更令我震撼,影像里写出了我们的现实。对我来说,所谓摄影不是现实的代替品,而是走向现实的必不可少的拐杖。”
安塞尔姆·基弗(Anselm Kiefer)也是在当代艺术上进行废墟叙事的重要艺术家。废墟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他要在画布上故意制造破败感,因为他说炸弹声就是我童年时代的塞壬,满目疮痍的城市就是基弗对世界的基本认识。他对神学和哲学有很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的作品中有种神秘的宗教感。基弗的作品总是要创造废墟,他有时候用火烧,有时候把火扑在画上,用泥沙填充;有时候就在画的创造过程中进行毁灭,在毁灭中生成新的东西;有时候用刀和斧头在作品上进行加工。他经常引用的诗就是他的思想来源,比如《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预见了耶路撒冷的灭顶之灾,但他的呼告并没有被人听取。基弗作品的出发点一直有一种毁灭感和一种压抑感,就像一个赤身裸体奔跑在旷野当中的先知,进行痛心疾首的呼告。 安塞尔姆·基弗
安塞尔姆·基弗
基弗对艺术创作的解释,对我们今天理解《逝物录》有非常大的启发。基弗这样说自己的绘画作品:我解除物质的外衣而使之神秘化。而这个其实也是理解沙朗斯基的很重要的一个通道。她描绘这12个永远逝去的物件或者是事件,其实是把它神秘化的,她构造了一个新的语境,解除了事物的原来的物质外衣。
还有一位法国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他2018年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做过展览,他处理记忆非常精彩。他说艺术家在一生的开始都会有些创伤,必须学会用艺术来疗伤。对于他来说,他的创伤就是屠杀犹太人的浩劫。因为他是犹太人,他的父母侥幸逃脱被送进集中营的厄运,但他身边的亲友有很多都已经在集中营中失去性命,所以他一直在追问自己,我如何被孕育?我为什么幸存?死亡到底是怎样的?所以在当时上海的展览里面,有很多非常精彩的关于记忆的作品。比如《无人》,像山一样大的一个衣物堆里面,有一个机器抓手,随机抓一件,移动到另外一处,这种命运的偶然性和被选择就能被体现出来。还有一个很浪漫的作品《机遇》,在很多芦苇上拴了小铃铛,这些小铃铛按照波尔坦斯基出生当日的星盘排列,在大雪皑皑中散发出声响。它是一个录像作品,当时没有人能到现场感受。可是他却抓住了那种气氛,非常浪漫。 波尔坦斯基作品《无人》
波尔坦斯基作品《无人》
最后,我再分享一个前两天看到的科学实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挺有意思的:
塔夫茨大学的科学家们发现,有一种生物叫扁虫,如果你切掉扁虫的头,它的头会长回来,还能恢复以前的记忆。通过研究扁虫在去头之前和去头之后在迷宫里面行走的导航路线来测试这一点,证明它们新长出的头能够记起切掉头之前走过的路线。里面还做了一个很残忍的实验,就是把其他扁虫的残骸,撒在地板上给其他的扁虫吃。新的扁虫会吃掉残骸,还会获得那些其它扁虫的记忆,并且用这些记忆帮助它们走出迷宫。听起来挺毛骨悚然的。但这个可能就是文学和艺术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看书,我们看的也是其他扁虫的记忆和碎片。我们吃下之后就获得了其他扁虫的记忆,而且通过这些记忆走出了迷宫。这是人类知识和经验以及对真理的追求经过代代相传之后的必然的美好结局。
所以,我是把塔夫茨大学的科学实验当做一个预言理解的。这也是呼应了《逝物录》:只要这些逝物还能够成为碎片进入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那我们就可以代替它们继续活着。而我们将来如果能够在别人的生命中得到延续,那也是一种很迷人的事情,不管以什么方式。 《逝物录》
《逝物录》
[德] 尤迪特·沙朗斯基 著
陈早 译
中信出版·大方 2020年4月阅读原文
新闻推荐
□王珉电影《少年的你》入选“2019中国影视剧年度影响力排行榜Top10,获2019中国年度新锐榜“年度电影”,获光影中...